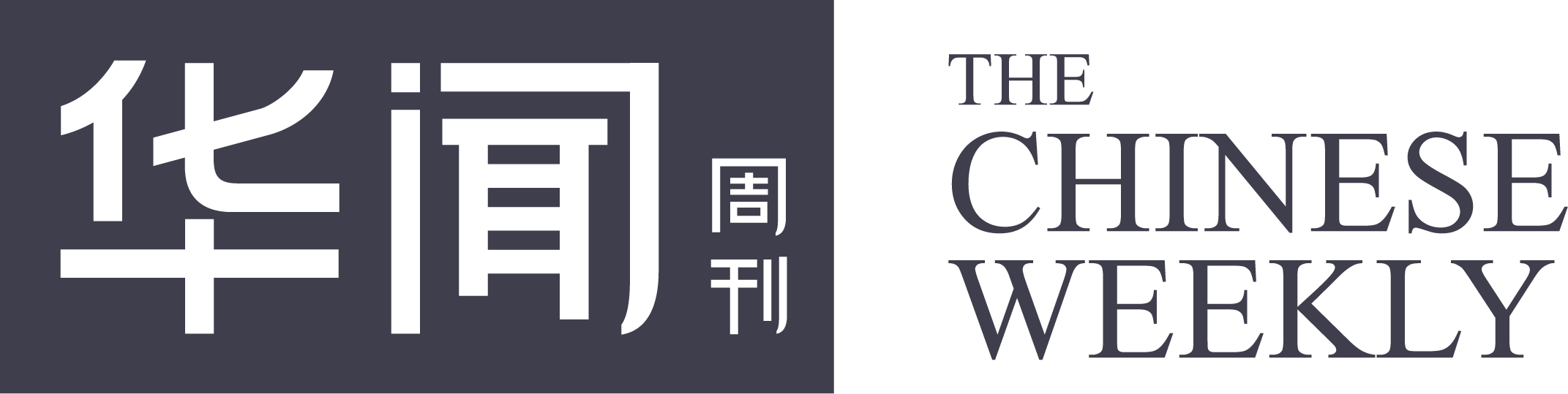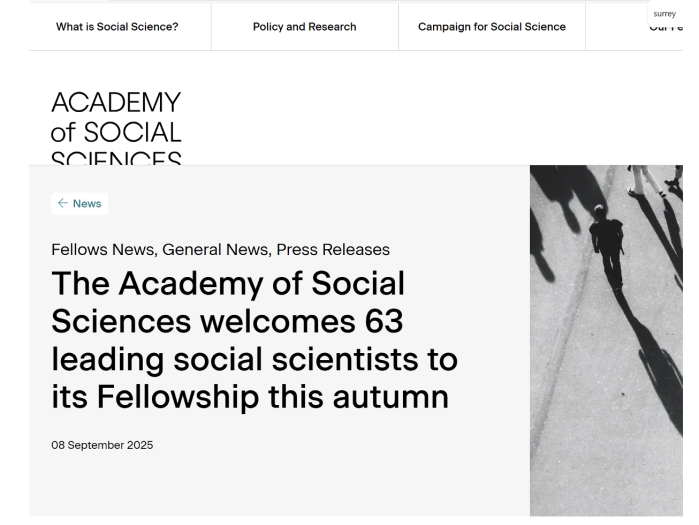寻找城市的角落
2010-12-31 00:00:00 1757 0 休学三年多的上铺哥们一天晚上跑来找我,随即便昏天黑地的胡乱聊了起来。他是患了忧郁症之后,在家静养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前些年脑袋接受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想得也多了,随后便夜里睡不着了。静养的方式,便是每天白天睡觉,晚上抽烟喝酒看球,旁的什么都不干。也难怪,他记性好得令人担忧,许多事情搁在脑子里,想忘,但却忘不掉,于是便要找人说出来。 他是个土生土长北京胡同里的人,脑子里装满了大杂院里头的故事。从小学同学做了混混,到外交官的儿子从阿根廷回来,帮家里开包子铺,面对这些故事,我完全不知所措。他神经质地拍着我的肩膀,轻声讲述着他家胡同前,那个变成了发廊街的菜市场,放佛随着城市消失的,还有他在这个城市的未来。“千万不要去那些地方,千万不要”,他时不时地重复着这句话,“北京变了”。我默默然地笑笑,试图找到他那迷离的眼神。怎么说呢,同这个城市,我没有血脉的联系。面对患着忧郁症的他,还有他脑海中的这个城市的一切,我永远都是局外人。 我在这个城市当了7年的过客,7年的局外人,而当我终于试图要记录我同她之间的历史时,我却即将离去。城市里的生灵们,大约总是面临着不得已的境遇。无论是过客,还是居民,都无法阻挡城市的变迁夺去他们各自的记忆。 我不晓得,记忆是否应当有所寄托。对于过客来说,离去便离去,城市在过客的脑海里,永远都是那幅固定不变的样子,倘若不再见,便也不应当觉察到失望。然而对于走不开的人们,目睹着他们所借以依托记忆的城市,不断地被现实抹去,随之而模糊的,也许恰是他们的记忆。害怕失去,便唯独只有逃离。 许多年前,当三峡周围的城镇即将被淹没之前,我跑去做了一个走马观花的旅行。许多年之后,忽然回想起当时印在脑子里的情形,却充满了遗憾。进而感慨竟然没有能够记录下那不断在消失着的历史的瞬间。我现在也时常会想起,那些被迫搬迁到新城当中的居民,那些无法逃离的、在老城镇中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们,究竟是不是会对眼前的现实产生一种迷离。新兴的现代公路,取代了那条通向码头的青石板路。他们坐在门口目睹的,既然不是那些来来往往的“棒棒”,那他们所看到的,难道还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交融了他们个人历史的城镇么?而丢失了历史的他们,是否还是他们自己呢?有时,我甚至嫉妒那个用忧郁症封闭了自己的兄弟,他坚守在那个属于自己的城市里。 在城市的风景当中,最为独特的抒情部分是人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风景和静物是抒情的,就好比侯孝贤在《悲情城市》当中,用长镜头锁住的那株在风中摇曳的树,那株只能属于那个时代、那群人、那个台北的树。在行将离开北京之前,我试图能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记忆。唯独用脚步踏过之后,陌生的土地才能属于自己。我同那个兄弟聊起了新街口,说我试图从阜成门内大街,一直向北走,去新街口找八道湾胡同。他不着边际地幽幽说:那个新街口,也不是原先的新街口了。先前那些和蔼可亲的临街店面,都面临着被归拢到新建大市场当中去的命运,而有了那么昂贵的租金,我相信,和蔼的店老板们,都将变得冷冰冰。我无言以对,因为即便像我这样的过客,几天前再回到新街口时,也竟然感到了那种在历史即将消失之前,人们的慌乱与无措。或许那些店主人们同这个城市的唯一联系,就是自己守候数年的店面。而今,他们不得不抛弃一切,被迫逃离。 好比M.Craft在那首Dragonfly当中唱道的一样,People coming people go。人总是来来往往的。害怕失去记忆,失去自己的人们便活在此刻,选择同他人联系在一起;而更加敏感的人们,选择把自己同城市连接在一起,幻想着城市能够获得比他们长久,能给替他们保存历史的记忆。而今,当城市也变得不可捉摸时,我们自己又将最终维系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