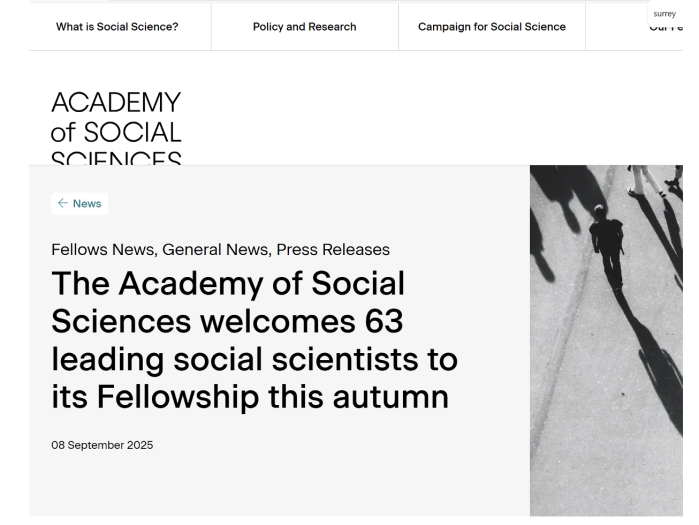试想,你花了一百英镑买了票入场,端坐在柯芬园皇家歌剧院,周遭都是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斯文观众,你正满怀热望、打算领略一场最正统、精纯的欧洲古典文化;幕启,映入眼帘的是一场淫乱荒诞的宫廷舞会、舞者半裸或全裸、追逐嬉闹、在壮大的序曲乐声中,你不敢置信地望着眼前这喧嚣失控的景象。 是的,这就是当代剧场鬼才戴维麦卡尔(David McVicar)一手打造的末世景观,煽动、奇幻、让观众坐立难安。 这位才四十四岁的苏格兰人,被票选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gay icon,是现今叱咤欧洲各大歌剧院的导演,柯芬园、大都会歌剧院、米兰史卡拉等一级殿堂,各各争抢要他。他所制作的剧目,从厚重的威尔第、艳情的比才、轻盈精巧的莫扎特到颠狂的史特劳斯,无一不精、部部都是话题,对于极力争取年轻族群观众的歌剧院而言,有了他就是票房保证。 十月底,深秋,一个清冷的夜晚,我前往了皇家歌剧院,又一次目睹了麦卡尔的幻术奇观,那不是法国文豪雨果笔下、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流韵事、不是十九世纪经典歌剧的华丽厚重,而像是一场希腊悲剧融合庞克摇滚的警世剧,暴烈炙热,却也凄怅悲凉。 这出威尔第的名剧《弄臣》,是麦卡尔在2001年制作版本的重演。当时才三十四岁的他,才气纵横张狂,把故事从原本贵气奢华的意大利宫廷,颠覆成了后现代、工业感、重金属的刚烈场景。舞台是金属材质的几何板块结构体,利用巧妙的平台回转装置,营造出内景外景交替的抽象空间。麦卡尔完全不打算粉饰太平,他直陈不讳地揭露人性恶淫败德的一面,在第一幕就全盘托出,阴沉、诅咒、严酷的视觉定调,与壮大的管弦乐对照,呈现出一股奇异的诗意与纯粹。 时序再往前推回到四月,同样是麦卡尔导演,同样在柯芬园,同样是威尔第的作品,只是这次换成了 《阿伊达》。 西方世界向来对古埃及有种莫名的迷恋想象,这部歌剧诞生于十九世纪,正值殖民主义盛期,东方主义的艺术表现达到顶峰,作为威尔第三大剧之一,过往的《阿伊达》制作,在舞台上总少不了浮夸的金字塔、棕树、异国情调的埃及服装,甚至动用几匹活大象以壮声势。 反骨的麦卡尔完全不打算这样做。他脑海中的古埃及,是个超现实的科幻场景,把这个说穿了就是个公主、将军、女奴之间纠葛三角恋的通俗剧,描绘城发生在异星球的悲壮故事。从来,以基督教为本位的思考逻辑,将任何非基督教的宗教、文化,说成是异端、异教、他者。作为西方文明源头,多神教的希腊文明尚且被称为异教,而古埃及更被视为异端中的异端,在这脉络下的潜义,就是败德、蒙昧、堕落。 麦卡尔把这层潜义与想象推到了极致。他的舞台上,演员不再穿着古埃及的传统服装,而更像是科幻片里沙漠星球的游牧民族,个个身着红黑色调的织物,包缠围裹,形体难辨。然而为了对照织物的堆栈,另有一帮群众演员,衣不蔽体,几近全裸,上演煽情群舞、酒池肉林、活人献祭、血浆流泻全身。那些男奴女奴、匍匐爬行、近乎动物性的动作……这一幅幅集体群像,让人联想起帕索里尼的禁片《索多玛一百二十天》。麦卡尔对身体景观的迷恋是显而易见的,当那些出身皇家芭蕾舞团、拥有完美比例身材的舞者在舞台上被剥光、那样直率张扬,你几乎觉得是一种挑衅,是才气纵横的导演施展权力,支配演员,挑战观众极限,挑战歌剧最为中上阶层文化指标,其所能被改革的维度。即使在当代民主社会,欣赏歌剧仍然是一项充满阶级优越的活动,位置优劣按照定价高低来区隔,但即便坐在最上层、最廉价票区块的观众,仍满是音乐品味挑剔的行家听众。他们来到这里,恭迎最一流的乐团、最拔萃的指挥、大腕歌剧演员,以及,无所预期的、爆炸性视觉奇观。 不只一次,舞台上的某景、某动作,让我身边的观众发出惊呼。《阿伊达》里的女二号,埃及公主,其造型让人瞠目结舌;半秃、披发、兽角般的金冠、一身红袍,粉白的脸庞绘有黑色线条、宛如边疆民族黥面。这个造型可说是全剧视觉调性的缩影:外星人般的超现实揉合原始文明的浓烈。 然而,如果只是视觉上的张狂,那不过是哗众取宠,麦卡尔的能耐当不仅于此。在情节的编排、演员互动情感的微妙,都可以看出他的功力。歌剧故事经常因为通俗肤浅为人诟病,但是维卡尔把情感面做大、把不合逻辑的过场做小,并且善用奇幻景观对比纯粹的人性情感,让故事有了近乎希腊悲剧的深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惯用的舞台设计风格,是以雕塑般的主体结构为舞台焦点,运用360度反转装置换景,因此观众不再期待传统的、2D式画版式换景(tableau style),而是结构转换后的柳暗花明,演员出场、走位也因此变得灵动随机。究竟麦卡尔有多抢手?今年在柯芬园作了两档威尔第《阿伊达》、《弄臣》以及史特劳斯的《莎乐美》,他即将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制作第三出威尔第《游唱诗人》。 作为当代最好的歌剧导演,他以前卫、金属、异色的风格,将歌剧从老殿堂解放出来。 作为同代观众的幸运之处是,我期待下一场石破天惊的煽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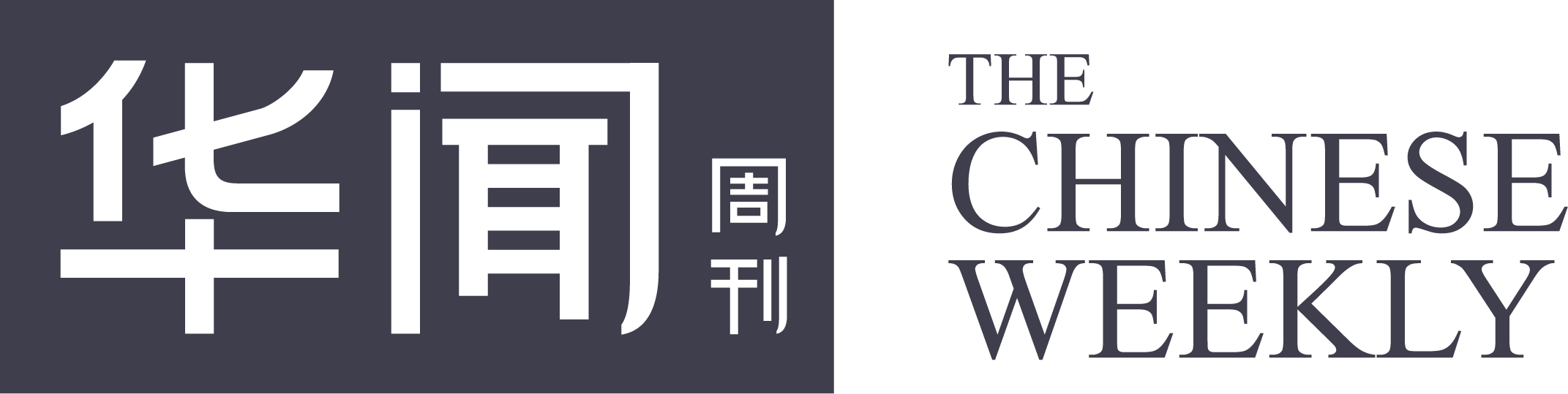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