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需要重提,最好不止一次去提,为了铭心,为了昭示。1942年,河南一场旱灾,致死300万人,同时使300万人背井离乡逃难,灾难深重。1942年河南大饥荒,是天灾与人祸双重打击下的产物。天灾状况,资料文献与媒体报道大致相同,无需多谈。值得细讲的是 “人祸”。让我们回到1942年初的那段时期。当时因通货膨胀,国民政府的征粮工作采取“征实”模式,即拒收货币,要求民众缴纳实粮。同时,整个征粮工作被分为征收与征购两大块。征收即按固定标准无偿向政府缴纳,征购则是政府按规定价格向社会上购买。之所以分做两大块,既为保证征粮数量,
更为保证粮食政策的平均和平等。1942年6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全国粮政会议,尤其强调后者。他要求“征购的数额要超过征收的数额,必须作到征收一分,征购一分以上”。因为征收针对全民,而征购主要针对有余粮的地主富绅: “征购多于征收,才能使小户负担减轻,而对于大地主富户要他多出余粮来应购,必须如此才符合我们粮食政策平均和平等的原则。”显然,蒋氏希望通过加大征购将负担更多地转移到“大地主富户”身上,以减轻“小户”负担。此次会议召开时,河南虽已有旱情,但尚未成灾,蒋氏也尚未得到任何关于河南灾情的报告。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上,河南军、政两家给了蒋介石两份矛盾的河南灾情报告。军粮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河南的军粮问题也列入讨论议题。蒋氏再度强调须对“富绅地主”加大控制力度。会议期间,河南灾情已见端倪。蒋氏也得到了报告,但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似乎截然相反。据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晚年回忆:“1942年秋的西安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按于氏的说法,蒋铭三、刘书霖给蒋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河南的灾情,而李培基则反之。
军、政两种报告,蒋氏究竟相信哪一种呢?就目前所见资料推测,蒋氏似乎取了折中值。换言之,因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互相冲突,蒋氏在本次会议上,对河南灾情的严重程度的估计是很不足的。西安军事会议,本是一个避免大饥荒惨剧的极好机会。此时灾情初发,河南军政要人也有机会向蒋介石报告真相。但因为军、政两方对灾情认知的冲突,这次机会被遗憾地错过了。
那么,当时作为河南省政府要员的李培基和经济学家卢郁文为什么不愿意向中央实情报灾?显然,李、卢二人1942年初执政河南这件事情,寄托着蒋氏在粮政方面的深切期望。蒋氏的信任与期望,对李、卢二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重的压力。如此,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在已经预知1942年粮食收成将不及1941年时,卢、李二人仍坚持不向中央报灾请求减免粮食征购。但身为经济学家的卢氏似乎忘了:1941年河南民众之所以还能在收获仅三成的情况下还能勉强负担沉重的军粮摊派,与1940年、1939年、1938年相对较好的收成是有关系的,民众拿往年的积累来填补1941年的空洞。
国民政府基层官员贪腐成性,为征粮不顾百姓死活也是导致饥荒带来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河南省许昌县长王桓武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预报当年许昌的农收为八成,不料旱、蝗连续成灾,麦的收成大都是一成许,秋收则还不到一成,富农还能够有些可吃的东西,贫户人家就不免饿肚子了。这还是灾况初成时的景象。王桓武为了做官,不敢实报灾况,只是狠着心按预报的八成数字催农人缴粮,缴不够的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因此农民不得不变卖家当,节衣缩食打发那些前来催粮的人。这其实对灾情来说就是雪上加霜。另外,赈灾时间太晚、河南三面受敌交通堵塞赈灾粮食运输艰难、乡绅富户们不肯出粮赈灾、各级赈灾官员贪污腐败,都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程度越趋严重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因素,就是河南省政府的救灾方式犯了方向性错误。本应该更多地利用民间资源来救灾,但河南省政府的限价政策,直接导致外省对河南的民间粮食贸易陷于停顿。
二十年前,因为发生在河南的这场灾难,刘震云写了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今年底,冯小刚筹划了十几年,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一九四二》上映,反映了那场发生在1942年河南的前所未有的大饥荒。这或许能给那段历史一个交代,但更多的还是需要人们对 “人祸”的时刻警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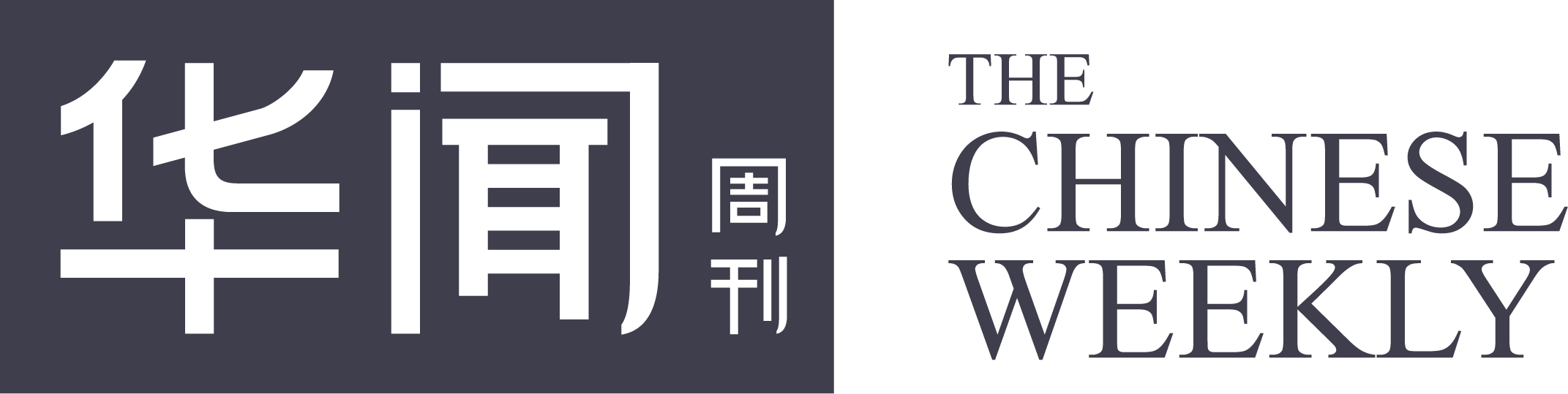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