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右)和波兰总理探访卡廷惨案发生地。就苏联时期发生的卡廷惨案,俄罗斯政府向波兰政府表达了诚恳的歉意并修建了新的纪念碑。(新华社/法新)
8月1日,英国政府公开了30年前的一批档案,其中英国女王在1983年准备发表的战争演讲引人注目。它打开了冷战时代的国家秘密,令每个英国人感受到昔日女王为国家命运的忧虑和担当的不易。这不是英国政府第一次解密,这则新闻也并没有令西方社会如何瞠目结舌。将尘封的档案解密是大英帝国正常的政府行为,也已经是英国百姓生活里惯常的事情。
去年夏天,我在上海古镇朱家角与一个酒吧老板爆发争吵,周游世界的他得出结论:毛泽东是他最为敬佩的天才伟人和政治家,现在的中国是非常开放和民主的国家,运行着地球上最好的政治制度。
持这样观点的人我见过不少,但一个不到三十岁便去过十几个西方国家的年轻人也这么看,我想不通。我耐心地问他的论据,他便以教科书般“正确”的内容予以证实,以他肤浅的所得所见所闻得出不干逻辑的结论。我耐着性子,举出更靠近真相的史实,告诉他那个军事伟人犯下的可怕错误;我又以我所掌握的西方民主常识与中国国家状况做基础的对比,分析国家强大和个体自由之间应有的平衡关系以及开放和民主的理想状态。但小伙子并不买账,尤其对60年大灾荒和十年文革浩劫中的死亡数字嗤之以鼻,让我拿出证据。我终于发起火来,告诉他考究的途径和援引的出处。他晒然摇头,轻飘地喝下半杯威士忌,说那只是文人们的江湖八卦,只要政府不说,算不得数。
那一夜很是懊恼,喝酒没了滋味,我为不能说服一个行了万里路的青年头疼不已。而更苦恼的是,我的确找不出丰富的权威档案来否定他错误的历史认知,就是于我自己,在看到互联网流传的那些“真相史实”的时候,不是也带着几分“出处不明”的怀疑吗?我在写《狗日的战争》的时候,常为找不到确凿的抗战史料而发愁,我能看到的大多有问题,关于“政治不正确”的部分基本上无迹可寻。作为个人,我无法调取阅读国家级档案馆的材料,也不知找谁去要,能要得到,估计也要挨过数不清的红章。教科书上的那些太过妖怪,甚至违背常识。每当有读者感谢我用小说“还原历史、给国民政府抗战以公道”的时候,我便愧意泛起,这只是在还原想象的历史,因为我很少见到国字头的“权威档案”。一个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的人,真不敢说我想象的猪长得像猪八戒还是牛魔王。
1992年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将最高机密档案的第一卷转交给了波兰总统瓦文萨,卡廷惨案至此天下大白,斯大林的一笔罪恶得以昭然。制造和执行惨案的俄方相关人已几乎全部过世,俄罗斯政府向波兰政府表达了诚恳的歉意并修建了新的纪念碑。
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惊讶俄罗斯人这份为前人之恶认罪的胸怀,也被这份可怕的档案历经半个世纪仍可重见天日感到神奇。它令我更清楚档案制度的意义,如果说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档案便是一个国家最后的文明操守,它守住一个民族最为真实的底线,让后人得以明白在那些分不清黑白的历史时刻里人性存在的意义。能够记下这档案的人是了不起的,能够保存这档案并解开的人也是了不起的。俄罗斯能使它重见天日,既是政治良知,也是大国自信。我想波兰人民不但不会因此增强仇恨,反而会对这只脱胎换骨的北极熊高看一眼。
而反观我国,我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后时代价值的档案被有效公布。1987年的《档案法》及其实施细则说得很明白,30年是个期限,该怎么解就怎么解。但我们看到,解开的档案大多无关历史痛痒,仿佛一个大户抛售一些没有存留价值的股票。而一切会在当今导致政治和信仰敏感的档案几乎一律不解,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也一概不解,仿佛也没什么机构能让档案局必须去解。它就像中国官员的财产状况,我们都知道有问题,但政府就不去系统调查和公布这个问题,你想自己去查,对不起,你违法。
新中国走到今天,几代人以青春和热血、甚至生命的代价换得不易的大国繁荣,但支撑这几代人无私奉献的信仰和理由,却是数不清的谎言和模糊如雾霾的传说。在半个世纪的发酵中,本是应该令当代人以史为鉴、继续前进的真实档案,反倒成了大白天下就会吓死个人的妖魔鬼怪。对于庞大而复杂的中国,这的确是必须考虑的大局。有些秘密必须是秘密,揭开它或带来意料不到的动荡,但如果没有良好的档案公开制度,共和国的历史如何真实传承,如何让后人以史为鉴再继伟业?
如今,我已经不再好奇黄继光是不是堵住了重机枪口;不再好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真是假;我也已经不好奇中国和越南到底谁是谁非;我甚至已经不好奇南联盟中国使馆为何被炸,因为当你面对一个秘密过多而且从来没有勇气面对历史真相的体制时,它说什么,我都不信。
以法律确立并保护的档案制度,是任何一个政府应该具备的最为重要的国家责任,无论对外还是对内,这份责任都与立国的根本和延续的制度文明有关。档案制度必须是国家制度的重要一环,因为时代一旦成为历史,便不会再有绝对的真相,它必须需要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不同档案记载方可基本还原。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将司马迁的《史记》看作历史,而他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楚霸王在乌江边全军覆没,无一生还,项羽与乌江亭长那番悲壮的对话,怎可能为他人所知?那定然是他在监狱里对江湖传闻的主观确认。没有严格完善的档案制度,真实史料的延续只能在口口相传中成为野史,后来学者即便再为勤勉钻研,沥血考证,亦只能揣度为先,战战兢兢记在纸上蒙混过关。如此看来,崔永元用百名老兵的讲述还原抗战历史,既是壮举,也是无奈,因为这些老兵生动却有可能片面的讲述,或许远比我们能够看到的史实更为可信。如果我们只能用当事人的老年讲述去破开一个又一个历史谜团,那无疑是这个东方大国制度文明的重大悲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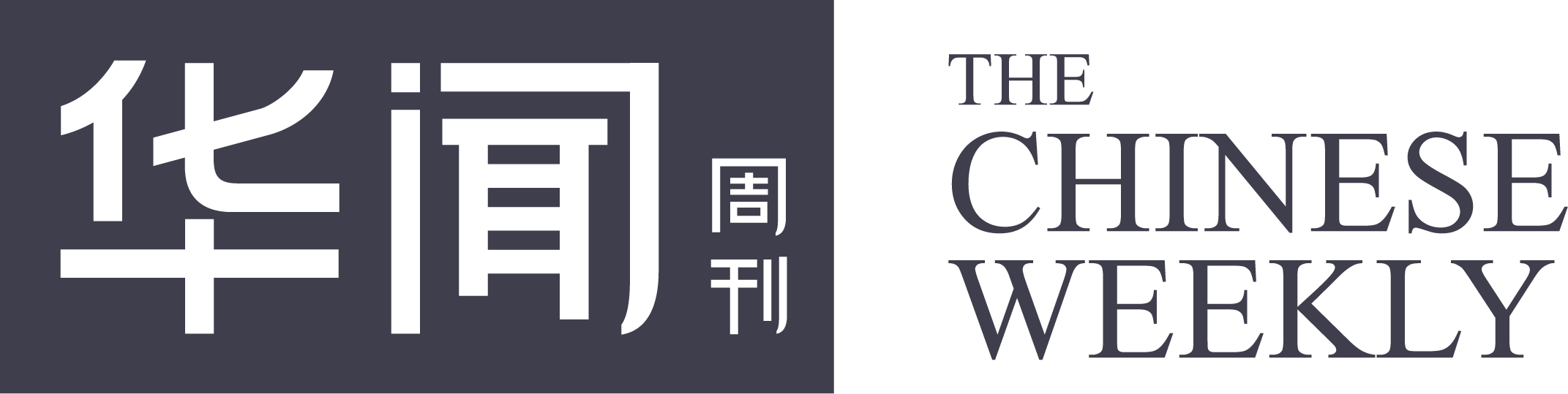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