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2005月1月1日零点的钟声敲响时,很多英国人已经进入了恬谧的梦乡,但一个叫做莫里斯·弗兰克尔(Maurice Frankel)的英国男人却心绪难平。
此刻,一种乐观的情绪占据了他的内心,让他激动而振奋。这一切,只因2000年通过的英国《信息自由法》终于在2005年1月1日这一天正式生效了。
作为英国“信息自由”运动的领导者,弗兰克尔在经过了逾20年的努力后,终于盼来了英国公共信息自由“有法可依”的时代。
根据该法,英国公众在获取公共信息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该法赋予了英国民众两项新的权利:有权利知道某个公共部门是否保存了某方面的信息;有权利获得这些公共信息。
在此法实行之前,所有公共部门的档案在未超过30年保密期或未被移交给国家档案馆之前,均被视为对公众“保密”的内容。而在该法生效后,公共部门的这些信息自其被创立之时起,甚至在被移交给国家档案馆之前,都可以向公众“开放”。除少数经批准免于公开的内容外,一旦有公众提出查阅申请,公共部门就必须向其公开相关信息。
“这将促使政府变得更加诚实。民众拥有了查看公共信息的权利,公共部门因此难以掩盖其不合格的表现,也无法通过编造或具误导性的陈述来逃避责任。” 弗兰克尔在2005年1月接受《卫报》采访时,表达了对于该法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的憧憬。
该法的生效意味着英国在公共信息管理“保密”与“公开”的“天平”上,“公开”的这一端又增加了极具分量的“砝码”。但从公共信息透明化的“英国路径”来看,虽然“有法可依”至关重要,但公共信息透明化又不仅仅是“建立起规则”这么简单。通过对该“英国路径”中各方力量相互推动、相互制衡机制的进一步了解,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启示。
规则是这样建立的
回溯到1838年8月14日,英议会通过了首个《公共档案法》,旨在“保护公共信息的安全”。不过,公共信息管理的“天平”此时更多地偏向了“保密”这一端。根据该法,英国公共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 Office)成立。该馆后来于2003年4月2日,和皇家历史手稿委员会合并,组建为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馆址设在丘园(Kew Garden)。
最初该法提及的“档案”仅指法律文件,并不包括政府文书。直到1845年,英国中央政府的文书才开始移交给公共档案馆保存。
但该法的重要局限也慢慢显露出来,它既没有明文规定政府部门必须将其公共文书移交给公共档案馆保存,也没有明确规定这些公共档案必须要对公众开放。
1952年,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开始对此前存在的法规进行检视。由于该委员会由英国前陆军大臣格里格爵士(Sir James Grigg)领导,因此也称被为“格里格委员会”。
“格里格委员会”通过调查,于1954年发布了基于调查结果的报告。
在该报告基础上,英国公共信息管理立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法规——《公共档案法1958》诞生,并于1959年1月1日正式生效。自该法生效后,公众查看公共档案的权利才首次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该法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变革,它首次从法律上规定了公众获取公共信息的“50年原则”。“50年原则”指的是所有移交给公共档案馆或其他由大法官指定地点保存的公共信息,除了少数例外的信息之外,在过了50年保密期后,可向公众公开。
1967年,威尔逊(James Harold Wilson)担任英国首相期间,该法进一步修订成为《公共档案法1967》,公共档案的保密年限削减为30年,并形成了广为人知的“30年原则”,该法于1968年1月1日生效。
值得一提的是,“30年原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涵义。第一个层面是对政府部门向公共档案馆或大法官指定的地点“移交档案”的最晚时限规定,即公共档案在年满30年后,其中被认定为值得永久保存的档案,都必须向公共档案馆移交;第二个层面,才是公共档案“保密年限”的规定,即公共档案在超过了保密期30年后,公众才可查阅。
当然,根据该法,那些可能“对国家形象、国家安全或外交关系”造成损害的公共档案,其保密期经大法官批准后可被延长。在判定哪些是免于被公开或可延期公开的“敏感信息”的程序中,大法官拥有主导性的权力,他有权应这些信息最初的提供部门的要求对其给予额外的保护。
“30年原则”的设立,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相关档案以及1923年以前的大批公共档案,在当时得以被公众所查阅。此后,在“30年原则”下,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批过了保密期的公共档案被“解密”,其中一些档案经过媒体的报道而广为人知。
在英国公共信息管理立法的历史中,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信息自由法》的通过及生效。1997年,英国大选中工党获胜,布莱尔(Tony Blair)当选首相。他执政的工党政府于1997年12月,发布了《公众知情权》(Your Right to Know)白皮书,并面向公众展开咨询。在其基础上,2000年,《信息自由法》通过,并于2005年1月1日全面生效(针对苏格兰地区的《信息自由法(苏格兰)》于2002年通过,同样于2005年1月1日生效)。
自此,英国公民可以随时依法提出申请,要求查看公共部门的公共信息。该法中提及的公共部门包括英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家医疗体系、公立学校、警察部门等。该法旨在增强公共部门透明度,使政府的政策制订更为公平与开放。
尽管该法也同时规定了8类可以“绝对免于公开”的信息范畴,以及17类“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才能决定是否公开的例外信息”。但相比于该法案实行之前的情况,仍然在公共信息“透明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信息自由法》推出后,在实践的层面上,大量公共档案在未满30年年限时即可对公众公开,事实上打破了原来的“30年原则”第二层面中关于公共档案保密年限的规定。但该法尚未对“30年原则”的第一层面“政府部门向公共档案馆或大法官指定的其他地点 ‘移交档案’的最后时限’产生影响。
直到2007年10月25日,时任首相戈登·布朗在演讲中讲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现在是来重新看看如何让公众查阅历史档案变得更加迅捷的时候了!”
布朗首相的这段话显然不是“无的放矢”,一项针对“30年原则”的独立复核在两个月后正式展开。2009年1月,该项独立复核的调查结果出炉,负责此项复核的保罗·戴斯(Paul Dace)在调查报告的开篇中说道:“自威尔逊政府将‘50年原则’变为‘30年原则’已有四十年时间,英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他所指的“变化”,包括数字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政府信息管理模式的冲击,以及各公共部门的进一步透明化。此外,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公民越来越多地希望了解公共部门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以及他们未来的政策是什么等等。
在该委员会看来,政府保护隐私的需求与民众了解政府工作愿望之间存在着必要的“张力”,该独立复核重点在于检视“30年”是否是维持正确张力的最合适年限。而复核的结果是,“30年原则”已经不再适应21世纪英国社会民主的需要,必须制定一个新的规则来维持以上所说的“张力”。该报告提出的新规则是将公共部门向国家档案馆移交公共档案的最晚年限,减少到20年。
2010年,《英国宪法改革与政府治理法》通过,其中已就政府部门向国家档案馆移交公共档案的最晚年限减少至20年,但该法的相关规定截至目前尚未生效。
不是“有法可依”那么简单
从英国走向公共信息透明化的路径来看,“有法可依”显然只是起点,而并非终点。“有法可依”只是建立了规则,但规则要得到充分的运用,首先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意识。根据英国政府官方数据,自《信息自由法》生效以来,仅英国中央政府每年收到的要求查看信息的申请就达到了3万起。在2005年该法生效的第一个季度,中央政府在20个工作日内,对公众申请的回复比例达到69%,在第三个季度达到81%。在2005年的前9个月中,中央政府向公众公开的信息达到了1.6万条。
除了民众的积极参与,公共部门及国家档案馆里的公共信息在“公开”后,要能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与传播,这需要新闻媒体拥有相当的报道空间,以便让诸多被“解密”的公共档案获得足够的曝光率。
仅从2013年8月1日最近“解密”的这批国家档案来看,从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前的细节披露,到女王原计划于1983年3月4日中午进行全国广播播报,而最终因预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而取消的备战讲稿,这些被“解密”的国家档案之所以能够被公众广泛知晓,与英国各大报纸、电视台的大范围报道有着密切的联系。
不可否认的是,公共信息透明化的背后同样有着英国各党派利益博弈及政党政治的复杂背景。
仅以《自由信息法》的出炉背景为例,就不得不提到1997年英国大选中,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在其竞选纲领中以“信息自由”为重要口号争取选票,并宣称“工党将致力于去集权化以及消除政府信息的过度保密,以此来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复兴”的政治背景。
当1997年5月,工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新上台的布莱尔政府大力推动“信息自由”的立法,正是对其竞选承诺的兑现。
民间压力团体在英国公共信息“保密”和“公开”的机制中,扮演的角色同样不容忽视。
莫里斯·弗兰克尔领导的“信息自由”运动组织创立于1984年,作为一个民间压力团体,在劝说政府推动相关立法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该组织还发布了《我们的知情权》手册,该手册到1991年被完善成《信息自由提案草案》。
当然,当“天平”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过于向“公开”一端倾斜,并开始透露出危险的讯息时,便有不同的声音及制衡力量出现,为“保密”这一端增添“砝码”。
伦敦大学学院曾经展开了一项研究,通过其研究结果指出了一个《信息自由法》被滥用的现象:在该法刚刚生效之时,有不少英国记者出于“试试新法好不好用”的心态提交了信息申请,这浪费了公共部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005年12月31日是个星期六,福尔克纳勋爵(Lord Charlie Falconer)也在英国报纸上撰写了一篇文章,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信息自由的本意是要赋予民众权利,而不是满足记者头脑发热的好奇心。”
正是英国司法系统、政府、民意、商界、学术界、民间压力团体以及媒体舆论的各方力量的权力制衡,使得英国公共信息的 “保密”与“公开”呈现出了一种“钟摆式”的平衡。如何持续地维持这座“天平”的平衡,令其不至于完全失衡甚至崩塌?这不仅是英国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样也值得世界各国深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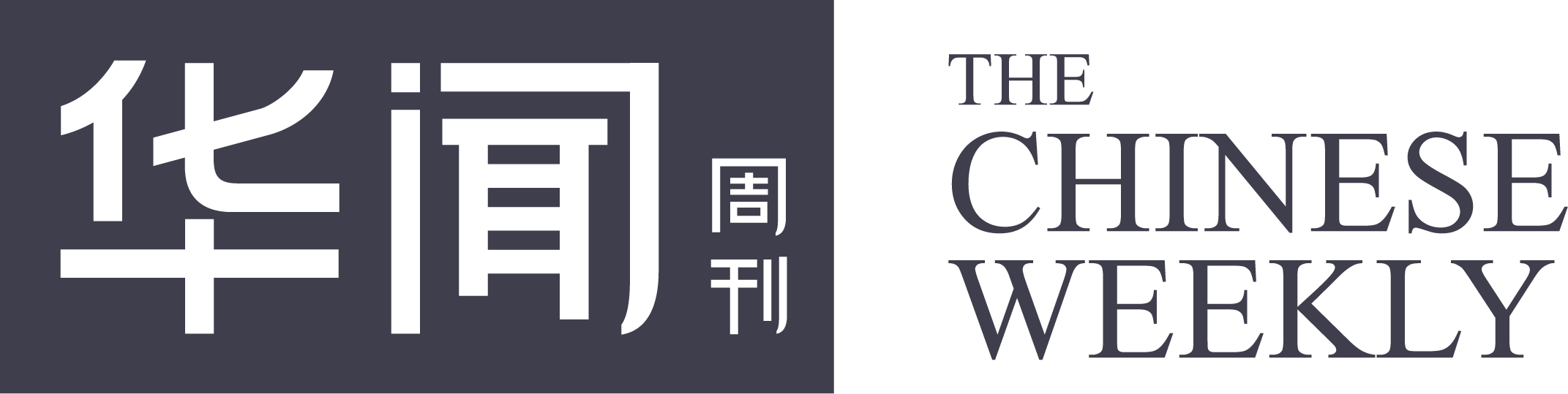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