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看到在叙利亚能够建立起一个‘伊斯兰国’”。十年前,在叙利亚的阿勒颇,一位美国记者访问当地一位名声鹊起的阿訇Abu al-Qaqa时,记录下了受访者的随想。
这位库尔德裔传教士当时一直在奔走鼓励当地年轻人“拿起枪,对抗美国人的侵略”。奇怪的是,受他感召,试图前往伊拉克等地参加“圣战”的,无一人遂愿成行。事后,情报机构揭开谜底:原来,这位阿訇只是当局用来试探民间潜在极端主义分子的“鱼饵”。
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阿訇的名字,但“伊斯兰国”真的由无到有,势大而起已成为了影响到全球的极端主义代名词。巴黎在《查理周刊》遇袭案发生的十个月后,于11月遭遇连环袭击,令这座欧洲之都乃至跨大西洋两岸的城市,风声鹤唳。中东和北非地区,一样难逃威胁。尤其是在西奈半岛,当地已经成为极端主义势力和反恐力量交锋的新战场。而对于新一轮的生死对决,身为主角的“伊斯兰国”已经就早前俄航坠机事件,对外得意自称,说服机组成员心甘情愿地暗藏爆炸物登机并不困难。

(12月3日,英国皇家空军已对在叙“伊斯兰国”展开首轮空袭。)
“还击”是西方主流社会在巴黎袭击凶案发生后,所释放出的共同声音。但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共同的疑问:“对于敌人,我们是否有了足够的了解?”
正如十年前,我在一场伦敦智库的记者会上,听一位西方记者质问来访的一位阿富汗高级军官,为什么阿富汗政府没有能力自行消灭塔利班?对方反问: “你又能说出多少个塔利班成员藏身的地名?”那位记者无言以对。
西方对于“伊斯兰国”的认知无外乎两方面:这是一个相信只有通过制造成功袭击,才能激起更多激进穆斯林加入的组织。此外,“伊斯兰国”的目的,正如其名,希望在世界各地都能召唤到响应者、追随者,建立势力更加庞大的宗教化、军事化的“哈里发”。
但事实说明,“伊斯兰国”较之前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对于世界安全所造成的威胁更大,而它的崛起和受支持的原因,也更加复杂。

(烽烟弥漫的叙利亚战场)
伦敦国王学院极端主义思想研究学者施拉兹·马赫尔(Shiraz Maher)和很多学者不同的是,他曾有过多次与支持“伊斯兰国”的“圣战者”面对面沟通的经历。在他的眼中,“伊斯兰国”的崛起对于世界,尤其是西方而言,是经历了多年的反恐战争之后,遭遇到的最大冲击,甚至可以说是挫败。在2011年,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军在巴基斯坦的突袭行动,已经让“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登毙命当场。那一年,很多人都为此庆祝多年的反恐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但直到“伊斯兰国”的出现,人们才意识到,早前的欢呼声响得太早了。
自幼发拉底河发迹的“伊斯兰国”从创立之初所营造的舆论氛围,如同 “共同开创一个新世界”,为其吸纳了心怀不同目的,怀揣不同能力的志愿者。对于这一点,英籍华裔青年黄磊比很多人都有更加直观的认知。

(英籍华裔青年黄磊(中)瞒着家人前往叙利亚战场,抢下“伊斯兰国”旗帜)
今年8月,在英格兰北部城市曼彻斯特,一个月前才从叙利亚返国的23岁的大学生和我面对面,诉说自己的经历。他在今年年初从电视纪录片上看到“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对无辜者的极端无情杀戮。他毅然决定瞒着家人前往叙利亚,加入当地库尔德民兵组织的国际志愿军,打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力量。
曾在英国陆军服役过的黄磊在对我描述当时所面对的敌人时,不住地用 “疯狂”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黄磊不止一次地看到十多岁的孩子或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举枪向自己冲来,令他一时间不知所措,只得“仓皇而逃”。他也曾亲眼看到一些少年身绑炸药向自己的战壕方向冲来,这样的自杀式冲锋景象,他从内心震撼看到麻木。
“这些人是为什么而战?”黄磊相信很多穆斯林是受到了“伊斯兰国”的宣传蛊惑,怀揣古兰真义,一心要改变中东乃至世界所有的社会不公。但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领导者在攻城略地时,连清真寺也烧毁,让数不清的年轻的穆斯林女性沦为军中性奴。
对于“伊斯兰国”的残忍,黄磊几乎是用生命的代价来了解的。他曾经有一次值夜班时想去距离自己不到20米处的地方小解。而就在他极速行进的时候,突然枪声响起,一颗从黑暗处射来的子弹擦着他的大腿动脉而过。黄磊说,虽然腿部负伤,但那一晚他一动不动地待在原位,直到天明。他知道,如果当时他呼喊求救,就会把自己的队友吸引过来,而黑暗中的狙击手可以如愿射杀自己的战友。而在此之后,最后一个面临死亡的,就会是自己。
黄磊说,敌方有很多身手不凡的狙击手。至于这些职业军人从何而来,按照当地人对他所说,和前伊拉克萨达姆政府有关,一些枪手原本就是昔日萨达姆总统的卫队成员。直到今年年初,这些人一直拿着每天450美元的丰厚佣金,嗜血战场,做着明日酋长的美梦。

(法国总统奥朗德亲自去机场迎接被“伊斯兰国”绑架的法国人,其中包括法国记者尼克拉斯·海宁(右二))
在2013年遭到“伊斯兰国”绑架的法国记者尼克拉斯·海宁(Nicolas Henin),在过去的十多年一直在中东地区做新闻报道。对于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外来职业武装者身藏在伊拉克以及叙利亚,获释之后的他在最近出版的 《圣战者学校——伊斯兰国的崛起》一书中也提到了萨达姆。在2002年到2003年,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面对美军为首的西方军事打击压力,呼吁全球各地的穆斯林都来支援。当时,有数百人前来响应,而这其中的很多人,在日后都成为作战精锐。
马赫尔以及海宁都认为,“伊斯兰国”地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地建起,本身就是“一石二鸟”的策略。它不仅可以吸引到更广泛地区的激进主义成员入伙,还能借机牵制住两个国家,以及它们背后更多的政治代理人。各方力量,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政府,也都看到了其中的玄机,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没有选择将雏形之中的“伊斯兰国”尽早扼杀。
正是因为有着先前各路极端主义组织所无法比拟的军事优势,“伊斯兰国”的势力在去年极速扩张。它在2014年,几乎一弹未发就长驱直入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同年,在悉尼和渥太华分别遭遇的恐袭事件,虽然不是“伊斯兰国”直接主导的行动,但却是当地极端主义者因为无法前往中东追随,而选择在本土发动的血腥行动。相比较在中东地区的攻城略地,西方国家境内所面临的本土极端主义威胁,更令当地人心慌。

(“巴黎恐袭”后,卢浮宫博物馆等旅游景区加强了安保)
“巴黎恐袭”发生后的第二天,前往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搭乘“欧洲之星”列车的乘客如往常一样平静,而在11月13日晚间,巴黎“小柬埔寨餐厅”发生的袭击事件中,失去丈夫的法国女人克莱恩,至今也没有走出伤痛打击。她在写给我的电子邮件里说,“法国现在很糟糕,而类似的处境在1961年之后,法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而对她而言,似乎世界已经彻底改变,除了像很多法国人一样待在家里,她哪里也不敢去,哪里也不想去。
从法国、西班牙,到英国、丹麦,这些欧洲国家在近些年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极端主义袭击,让外界感到数不清的“圣战者”就生活在自己的城市。为了不让巴黎袭击案这样的惨剧重演,欧洲正在重新考虑26国无边界约束的申根政策,与此同时也在研究如何不再被斯诺登案的困扰所累,不再因为担心情报泄密而放弃多国间的情报共享。如比利时前首相居伊·伏思达(Guy Verhofstadt)所言,恐怖主义是无疆界的,情报工作也应是如此。
但是否控制住边境的自由流动,看到英美等国的“五眼”情报共享机制在更广泛的盟国间复制,极端主义袭击就会销声匿迹呢?布鲁塞尔郊外小城莫棱比克(Molenbeek)的现状其实已经给了外界最现实的答案。

(早前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莫棱比克区,当地居民手持写有“我爱莫棱比克”字样的标语,参加悼念集会)
叙利亚战事让我们已经不容易前往幼发拉底山谷,探寻“伊斯兰国”的起源;但从布鲁塞尔驱车前往莫棱比克却并不困难。这里是比利时警方11月才因为追缴巴黎袭击案凶嫌,突击搜捕过的城市,而这里也被外媒称作是“恐怖主义在欧洲的心脏”——在不同时期,居住在这里的包括在2001年杀害阿富汗反塔利班北部联盟指挥官Ahmed Shah Massoud的“基地”组织成员;还有人曾参与2004年马德里火车爆炸案;去年,这里的一位居民还曾前往布鲁塞尔的一家博物馆杀死四人;此外,今年8月份在阿姆斯特丹至巴黎的高铁上,意图制造极端主义袭击的成员中,其中一人也是住在莫棱比克。就连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都承认,“几乎每一次袭击案,都会同莫棱比克有联系”。
弗莱芒语区小城莫棱比克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恶人谷”?除去那些已经出现的犯案者,当地的多数外来移民和涌入其他欧洲城市,憧憬未来生活的移民没有区别。但就连一些西方媒体也承认,莫棱比克虽然地处比利时这个西欧富庶国家,外来移民却长年备受高失业率,种族歧视的困扰,很多外来移民虽然积极融入当地的社会,但最终还是失望地发现,水油难融。其实在其他一些欧洲城市,我也听过类似的故事。像是在英格兰的港口城市朴茨茅斯,当地廉价服装店的穆斯林员工因为不满生活现状,悄悄潜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
面对这些人、这些事,《经济学家》评论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令社会各阶层都意识到,保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符合自身利益。英国首相卡梅伦早在2011年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就明言,英国历任政府实施的多元文化融合政策已经失败。
有中东政府消息人士对我透露: “最多还有两个月,‘伊斯兰国’就将不复存在。”但我怀疑这是否又是一次太过乐观的判断。我相信,作恶必遭惩“伊斯兰国”不可能长久不灭,但此时“风头”似乎被“伊斯兰国”盖住的“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u)和“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Ahrar ash-Sham),这些早已被世界多国政府列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极端力量,是否有朝一日会成为又一个 “伊斯兰国”?
本文出自《华闻周刊》第200期精装杂志,原题:弄懂“伊斯兰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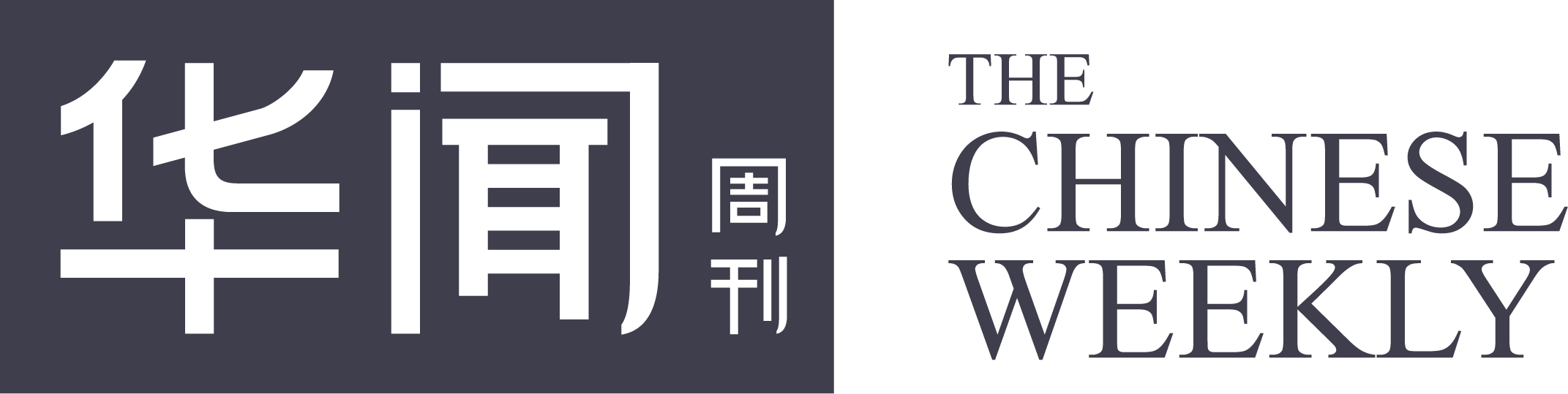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