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出发,颠簸了3个小时后,我们在汤顿(Taunton)的火车站见到了匆匆赶来的约翰(John),一见面他就操着浓重的贵州口音普通话尝试和我们交流。我们从火车站步行到他家,一路上他聊起了自己和妻子凯瑟琳(Catherine)共同领养的孩子的情况。
他们领养了5个中国孩子,其中3个有残疾。我们到达时,二女儿梦晓(Elsie)来给我们开门,在约翰的引导下,她腼腆地给我们打了招呼。这是一幢临街的房子,他们三周前刚刚租下。穿过暗暗的过道,我在客厅里看到了其中两个孩子。
一个皮肤白皙红润的孩子直直地躺在临门的沙发上,身体软软的,不能灵活动弹,他是约翰夫妇最小的儿子,名叫辉川。另一个孩子歪着头坐在沙发上,他的眼睛直直地望着我们,眼神中流露出的是一股毫不畏惧的神气,他的中文名叫福刚。约翰夫妇给辉川起名叫Joel,给福刚起名叫Theo,因为他们坚信两个儿子都是上帝赐予他们的礼物。
凯瑟琳在与客厅相通的厨房里忙活,听到我们来了,擦了擦手赶紧出来打招呼,问我们喜欢喝什么茶。一阵寒暄之后,她又回去忙活了。我听见不知来自哪里的低吼声,于是循声找去。在客厅内侧半掩着的一扇贴有“爱”字蜡染布的门里,看到了三女儿甜甜(Esmei)。
她躺在一片厚厚的毡毯上,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头一直四处晃动着,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吼叫。凯瑟琳闻声赶来,她连声对我们说抱歉,得给甜甜换衣服了。甜甜每两个小时需要一次检查,每天都需要私人护理,几乎每分钟身边都离不了人。而由于刚出生就被遗弃,出生报告也语焉不详,送医院检查后也未能诊断出准确原因,他们不清楚甜甜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至此,我已见到5个孩子中的4个,却没有见到约翰口中一直念叨的大女儿。在我的询问下,约翰领我去餐厅见大女儿新婷(Evie)。餐厅没开灯,英国灰蒙蒙的天让餐厅显得更暗,新婷蜷在餐厅角落的沙发,玩着iPad,瞥见我们进来,她把头又略低了低。我们和她打招呼,她并没有回应。
约翰开始介绍着,并让她告诉我们她的中文名字,她抬头望向约翰,似乎在笑,又似乎没有,用一口流利的英文:“我不会说的。”无奈之下,约翰只得自己告诉我们,他们在2001年底从江苏高邮的儿童福利院领养了她,那时她才10个月。今年快14岁的她随约翰夫妇在中国生活了近7年,在英国待了7年,这使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中文也很棒。
约翰告诉我,继领养新婷之后,他们在2004年领养了二女儿梦晓。他们自己养育了3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在新婷来到他们家的时候,他最大的孩子15岁,最小的才13岁,因为他们夫妇工作忙,孩子们都轮流担起了照顾新婷的工作。
谈起当初去中国跨国领养,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原因,约翰笑着回答“为什么不呢?”夫妇俩的一个英国朋友此前领养了一个中国小孩,她向夫妇俩讲述了许多关于去中国领养的故事,加上对中国一直兴趣浓厚,于是他们开始做各种关于去中国领养的研究。约翰此前学的是小学教育专业,在小学教了25年书,而凯瑟琳则是特殊儿童教育方面的专家,一直在照顾特殊儿童。考虑到他们自身的专业及工作背景,夫妇俩觉得自己能胜任领养两个孩子之后的工作。
领养了新婷和梦晓,他们如获至宝。一直想回馈中国带来了这两个宝贝的恩赐,他们在2007年飞赴中国,想为中国的孩子们做点什么。在北京某儿童救助中心一位女士的引介下,他们来到迫切需要他们的贵州贵阳,在人生地不熟的欠发达地区筹建起儿童救助中心,帮助当地福利院照顾一些残疾孩子。当地人们对残疾儿童的认识非常有限,他们的到来帮助了很多受苦受难的孩子。
甜甜、福刚和辉川就是在贵阳时领养的。在所有的福利院里,身体健康、可爱和漂亮的孩子是最容易被领养的,而残疾的儿童则鲜有人问津。大多残疾的孩子都是被外国公民领养,而一些重度残疾的孩子则会被留在福利院里。
因为贵阳的福利院对特殊儿童的照顾依然不成体系,工作人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加上有些残疾的孩子被当地人认为会传染疾病,所以他们在那并未得到最妥当的照顾。约翰夫妇的救助中心担起了这个担子,夫妇俩都有专业知识背景,他们把英国先进的护理知识和教育理念带到那里,培训招募来的工作人员,亲自照顾残疾的孩子们,一带就是十来个。
在所有留下的孩子中,甜甜、福刚和辉川一直没有被领养走。约翰夫妇从甜甜3岁起开始照顾她,3年之后,即甜甜6岁时,约翰夫妇收养了甜甜,在2013年夏天正式领养了她。他们也分别在2010年和2014年领养了时值3岁和4岁的福刚和辉川。
和大多数领养家庭不一样,约翰夫妇领养这三个孩子,并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人来领养走他们,而此前这三个孩子一直跟在他们身边,由他们照顾,培养出了感情,于是他们决定肩负起这个重担。
看着坐在轮椅上撕咬着衣服的甜甜,我问约翰:“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吗?”他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一旦正式领养,就是一个很郑重的承诺。”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去制止甜甜咬自己的裙子。“对甜甜来说,这个承诺是一辈子的。她永远不可能独立。”
看着甜甜一次次被约翰夫妇梳好又一次次被她自己弄乱的头发,还有她始终无法聚焦的眼睛,我不由担心起来,毕竟约翰夫妇已然年过半百。我委婉地问约翰:“等她50岁了,依旧无法独立,那时该怎么办?你们考虑过吗?”约翰一脸惋惜:“我想她也许只能活到30岁左右,也许更短,因为通常像她这类的病人,寿命会非常短。”
他补充道:“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周全。领养她的时候,英国政府有要求我们填监护人,就是万一我们不在了,由谁来代替我们照顾他。我大女儿签了字。”他是在说他和凯瑟琳亲生的大女儿,现在也在从事特殊儿童的护理工作。
此时采访进行到一半,凯瑟琳已经忙活了好一阵子,她为一大家子人准备好了午餐。考虑到英国冬天黑得早,加上阴雨天气导致房子里光线差,约翰夫妇不得不在此时召集起5个孩子来拍摄全家福。
在听到爸爸的呼唤声后,两个女儿——新婷和梦晓来到了客厅。和妹妹梦晓一起时,新婷似乎一改此前的内向。她从妹妹手中拿过我们带去的上一期《华闻周刊》杂志,翻阅起来。约翰和凯瑟琳分别抱来了甜甜和辉川,也唤来了福刚。由于甜甜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晃动,凯瑟琳抱她坐到沙发上,试图控制她的身体;而小儿子辉川由于身体太软,脑袋无法直立,约翰不得不采用了一个利于扶住他脑袋的姿势来拍照。
拍摄进行得并不容易,因为纵使我用了凯瑟琳教的各种方法逗甜甜看镜头,她还是一次都没有看向镜头的方向,而辉川的脑袋则需要约翰一次一次地扶正,好在约翰夫妇一直在辛苦地尽全力配合。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此前在餐厅明确拒绝了约翰的拍照邀请的新婷,在摄影师的每一次“三,二,一,茄子”时都拿出了她最甜美灿烂的笑容。而小儿子辉川,虽然脑袋需要被一次次扶正,但脸上露出的却是孩童最天真无邪的可爱笑容。
完成了合影拍摄后,凯瑟琳招呼大家一起去餐厅享用午餐。为了拍摄好一家人用餐时的场景,尽管约翰夫妇再三盛情邀请,我们还是没有加入他们。在简单的祷告之后,约翰夫妇和孩子们开始用餐,新婷、梦晓和福刚都可以自主地吃面包和培根,辉川太小,凯瑟琳喂给他调好的米羹,而约翰则负责给甜甜喂吃的,在给甜甜喂食的间隙,约翰才忙不迭地给自己塞几口。
午餐结束得很快,福刚跟梦晓说着什么,因为他吐字模糊,我一个字都没听懂。可小姐姐梦晓却全懂了,她一口漂亮的英语:“你拿了一上午了。”我一头雾水,在约翰的解释下才明白,俩姐弟是在抢iPad呢。
在欢笑声中,我和约翰又回到了客厅继续聊天。新婷、梦晓和福刚一起帮妈妈收拾餐具,福刚行动并不方便,走起路来也有些趔趄,看他端着盘子来回于餐厅和厨房,我很想上去帮一把。此时约翰接着用餐前的话茬说起来,他指着步履蹒跚的福刚,说:“他迟早能独立的,你看现在。”他又转身抱起正在憨笑着的小儿子辉川,说:“将来某天他应该也能,可甜甜不会。”
看见甜甜还在不屈不挠地扯咬着各种东西,他放下小儿子辉川起身制止她,将她从轮椅上抱上了沙发,塞给她一个缀满各式玩具的布包,并在她额上深深一吻。那个布包上有像甜甜这样的孩子需要的一切玩具,比如可以供她咬却不会伤害她的软质玩具,还有小铃铛之类孩子喜欢玩的东西。
在我们聊起很多他们的领养故事和在中国建立救助中心的经历时,约翰不时地向在厨房里忙碌的凯瑟琳征询意见,“凯西,你同意我这么说吗?”“凯西,你记得那具体是在几月吗?”此时凯瑟琳就会出来跟我们聊上几句。说起在贵阳的生活时,凯瑟琳激动地跑出来,她有个看牙医的故事要分享。“他们真的是在用锤子锤我的牙,锤了半个小时,我看见血肉模糊的一盘,都以为自己要死了。”
医疗条件并不是最令他们无法适应的,因为他们的不同肤色在当地甚是罕见,会有当地人凑到他们面前问他们是哪来的,拿起他们购物篮里的食物说,“你吃这个呀?”当他们领着孩子们上街的时候,甚至有行人直接跑过来指着他们,称他们是“拐卖孩子的”,高呼“这不是你的孩子”。约翰对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司空见惯了,他甚至能拿这些尴尬事来打趣,但他也坦言自己对“这不是你的孩子”这种话还是介意的,因为在他心里,他们每一个,就是他自己的亲骨肉。
听约翰和凯瑟琳以一种戏谑的、近乎可爱的姿态来给我讲述这些故事,我甚至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七年。这七年,他们夫妇学会了一口不那么流利的贵阳话,喜欢上了中国的食物,还有那些听起来并不礼貌的当地人。凯瑟琳特地拿出他们千里迢迢带回英国的几瓶“老干妈”豆豉酱给我看,而约翰也找出了他们和当地人的合影。
“他们不是不友好,只有未受过正规教育,不懂社会礼节。”约翰替他们解释道。
这七年里,约翰告诉我,最大的困难一是由于中国的残疾人通道系统设置得不够全面,他们带孩子出门非常辛苦;二是中国的签证政策规定他们只能在中国本土续签一次,此后每年他们都得拖家带口地把所有孩子带回英国,在英国续完签证之后再回到中国去。
昂贵的机票和签证费对这个大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而他们在中国七年的服务是完全义务的纯志愿工作,他们生活的来源,仅仅全部倚靠约翰夫妇为救助中心募来的一些资金以及一些善心人士的帮助,这样的大笔支出对这个家庭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约翰已经七年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了,可他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谈起跨国领养手续存在的问题,他抱来了一大沓领养文件和领养证书,摞起来大概有两三本《辞海》那么厚。“严格、严谨是好事,但手续真的太繁琐了,领养一个孩子至少都要两到三年时间,并且太贵了。”他说。“领养一个孩子至少要9000磅费用,每个地区不一样,上不封顶。”在他看来,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生活确实非常重要,“但没有必要将标准设置得高不可攀,这样打消了很多家庭跨国领养的念头。”他评论道。
交谈过程中,甜甜在一旁叫吼着,似乎是哭了起来。凯瑟琳闻声而来,她和约翰都向我解释:“这是她表达自己愤怒的方式,她不会说话,智商是6-8个月婴儿的水平,她用吼声来表达情绪。”凯瑟琳给她替换被弄脏的衣服,而我为了让她停止哭泣,开始讲起中文,凯瑟琳说她虽然听不懂,但是喜欢听。
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凯瑟琳提前走了一步去看她在中国受尽折腾的牙,而约翰也推着福刚要去看医生。他说他染上某种对孩子有一定危险性的病毒,他脚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他招呼梦晓来照看弟弟妹妹,梦晓熟练地把弟弟辉川放倒在沙发上躺好,给他盖上了毯子。我和依旧蜷在餐厅角落沙发上听歌的新婷打招呼道别,她羞涩地笑了笑,向我道别。
快走到火车站,我们看着匆匆离去的约翰的背影消失在夜幕中。他告诉我,因为希望更多的孩子得到帮助,他打算加入位于伦敦的跨国领养指导中心,好在英国的福利政策好,对残疾儿童的支持力度高,他打算将甜甜送到特殊学校学习,这样有更专业的人能够照顾她,他和凯瑟琳也可以结束身兼父母、保姆、护工和老师数职的状态,专心当好父母。他们也打算卖掉位于康沃尔(Cornwall)的房子,在这里买一套适合孩子们住的房子,让他们能更舒适地生活。
约翰夫妇的亲生儿女也都在从事特殊儿童教育行业,在他们一家的世界里,似乎没有“利己”这个词。七年的志愿服务,七年没更新的衣柜,每日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终生的承诺和奉献,似乎都只是为了爱。
本文出自《华闻周刊》第189期精装杂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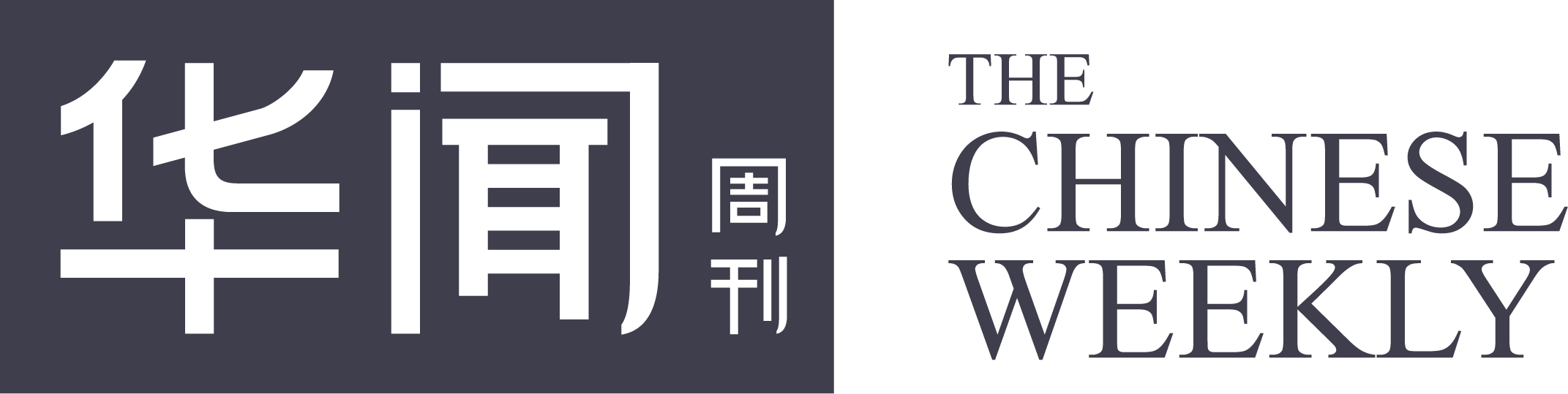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