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舍在作品中提到的伦敦地名透露着一股子“京味儿”,比如他把牛津街西端的Marble Arch称为“玉石牌楼”,把商铺云集的Oxford Circus译为“牛津圈”,把离大英博物馆不远的Gordon Street叫做“戈登胡同”,别有一番“洋为中用”的幽默。当我路经这些地点之时,想起老舍的所记所述,便觉意趣盎然。
从伦敦市中心乘地铁中央线到荷兰公园站下车,步行穿过数条街巷,便到达了圣詹姆斯花园街31号。
抬眼看去,这是一栋翻新过的维多利亚式黄砖联排建筑,算上地下室共四层,高阔的台阶从街面向上直达大门,深绿的底色上镶嵌着金字门牌,黑色的铁栅栏围出英国式的秩序感,克制而内敛,是伦敦中产阶级家庭常见的住宅风格。
在明亮的轩窗之下,一块“英格兰遗产”的蓝牌挂在乳白色的外墙之上,上面铭刻着老舍姓名的中文、拼音、他的生卒年以及居住于此的时间,此牌挂于2003年11月。
“蓝牌制”是英国保护名人故居的制度,能获得“挂蓝牌”殊荣的名人故居必须符合一系列严苛的条件,比如该名人在其所处领域是公认的杰出人物、为人类进步和福祉作出过重要贡献等。老舍是迄今为止唯一在英国获此殊荣的中国人。据老舍之子舒乙的回忆,这里能被挂上“蓝牌”,其实也颇费了些周折。
英国子午文院院长苏立群在为本期《华闻周刊》撰写的《我与“老舍”的缘分》一文中提到,1990年代舒乙随《二马》电视剧摄制组来英时,老舍故居尚未被挂上“蓝牌”,苏先生在与舒乙聊天时,还曾抨击英国人“对外国在英的人文财富不闻不顾”。好事多磨,舒乙后来与对老舍作品有深入研究的伦敦大学、大英图书馆、爱丁堡大学的5位汉学家共同申请、推动,才最终促成了此事。
1924年至1929年,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前身)任教,在伦敦度过了他25岁到30岁的时光,他在伦敦的故居有好几处,被授予“蓝牌”的这一处,是老舍在伦敦期间租住时间最长的居所。
看到老舍这个位于伦敦富人区的故居,或许有人会以为八十多年前他在此过着稳定、富足的生活,其实不然。我在现存的一些有关“老舍在伦敦”的文字记载和史料中发现,老舍在东方学院任教的薪水微薄,最初年薪只有250英镑,三年之后才在他的要求之下涨到了300英镑。
在1920年代,老舍与英国人艾支顿(Clement Egerton)合租的是此栋楼的第三层,老舍出餐费住小间,艾支顿出房租住大间。艾支顿是何许人也?他是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将中国的《金瓶梅》翻译成英文的人。
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的C层找到了这个版本的英译《金瓶梅》,硬面浅绿色,共四册,出版于1939年。这个英译本取名为“金莲”(The Golden Lotus),亚非学院书架上现存的是一部半。所谓一部半,就是有一部是1-4册齐全,另外还有半部只剩下了其中两册。在书的扉页上,艾支顿特意对中国室友舒庆春表示了感谢。他说:“我在此特别向舒庆春先生致谢。他是东方学院的中文讲师,在我着手翻译此书的时候,如果没有他不屈不挠的慷慨帮助,我根本没有勇气接受这个任务。”
除此之外,在致谢页的前一页,艾支顿还特意写了“To C. C. SHU, My Friend”(即献给舒庆春先生,我的朋友)字样。舒庆春(Ching Chun Shu)是老舍的本名,他在受洗加入基督教之前,一直用这个名字,受洗之后,则改名为舒舍予。在1924年,老舍称自己过了“关”,所谓过了“关”,就是他正式受洗加入了基督教。老舍后来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也是因为在教会中结识了燕京大学神学院英国教授易文思,在他的推荐下来到了英国。
在今天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里,人们不仅将老舍作为一名著名的中国作家来纪念,更将其视为在外汉语教学的前辈。在为本期《华闻周刊》撰文时,任教于亚非学院的崔燕博士说:“老舍先生培养了一批批懂得汉语的人材。我们今天的汉语教学可以说是在老舍当年打下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在后来的散文中,老舍记述了自己对伦敦和伦敦人的第一印象:“车站上,地道里,转运处,咖啡馆,给我这么个印象:外面都是乌黑不起眼,可是里面非常的清洁有秩序。后来我慢慢看到,英国人也是这样。脸板得要哭似的,心中可是很幽默,很会讲话。他们慢,可是有准。”
提到饮食,他则说:“饭是大块牛肉。由这天起,我看见牛肉就发晕。英国普通人家的饭食,好处是在干净;茶是真热。口味怎样,我不敢批评,说着伤心。”(见《头一天》)
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图书馆里,老舍创作了三部小说,即《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的大部分。谈到这三部小说的创作,老舍回忆说:“假期内,学院里清静极了,只有图书馆还开着,读书的人可也并不甚多。我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与《二马》,大部分是在这里写的,因为这里清静啊……哼,希望多咱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这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
他在《我的创作经验》一文中也提到,在伦敦的生活是促使其成为小说家的机缘:“倘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为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地念小说,拿它作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了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呢?”
老舍在伦敦创作的这三部作品,不仅奠定了他之后的文学语言风格,也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当然,除了英国,老舍还先后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新加坡以及美国等多个国家游历、生活或讲学,可说是近现代较早游历世界各国的中国人。
海外的生活以及与世界各国文化、社会、思潮及民众的近距离接触,使得老舍的创作融会东西、兼收并蓄,在世界性和现代性的语境映照之下,他的作品进一步彰显出了强烈的民族性与本土特色。老舍在作品中提到的伦敦地名就透露着一股子“京味儿”,比如他把牛津街西端的Marble Arch称为“玉石牌楼”,把商铺云集的Oxford Circus译为“牛津圈”,把离大英博物馆不远的Gordon Street叫做“戈登胡同”,别有一番“洋为中用”的幽默。当我路经这些地点之时,想起老舍的所记所述,便觉意趣盎然。
但具悲剧性的是,1966年8月23日,在红卫兵将老舍从北京市文联办公室押往孔庙并将其毒打之时,旁人揭发老舍的罪状之一,竟然是“崇洋媚外”。
老舍在发表于1943年的散文《诗人》中曾说到自己的生死观:“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1966年8月24日,在于孔庙前受毒打后的第二天,他被发现自沉于北京太平湖,同样是“投水”、“殉难”,实在令人唏嘘。
老舍曾经说:“我写过《骆驼祥子》。那是因为,那时的世界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位置的世界。”
在英国居住多年的华人,或许还依稀记得2003年11月25日老舍故居举行“蓝牌”揭幕仪式的新闻。11年过去了,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然不同。我站在这栋挂着“蓝牌”的老舍故居前,倍感冷清与寂寥。
路人匆匆而过,对于我在此伫足,投来不解的目光,或许他们并不清楚这位中国作家是谁、他写过什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处于何种位置。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前,我们又何曾清楚自己是谁、身处何方?
本文为《华闻周刊》原创文章,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内容合作,请发送电邮至:[email protecte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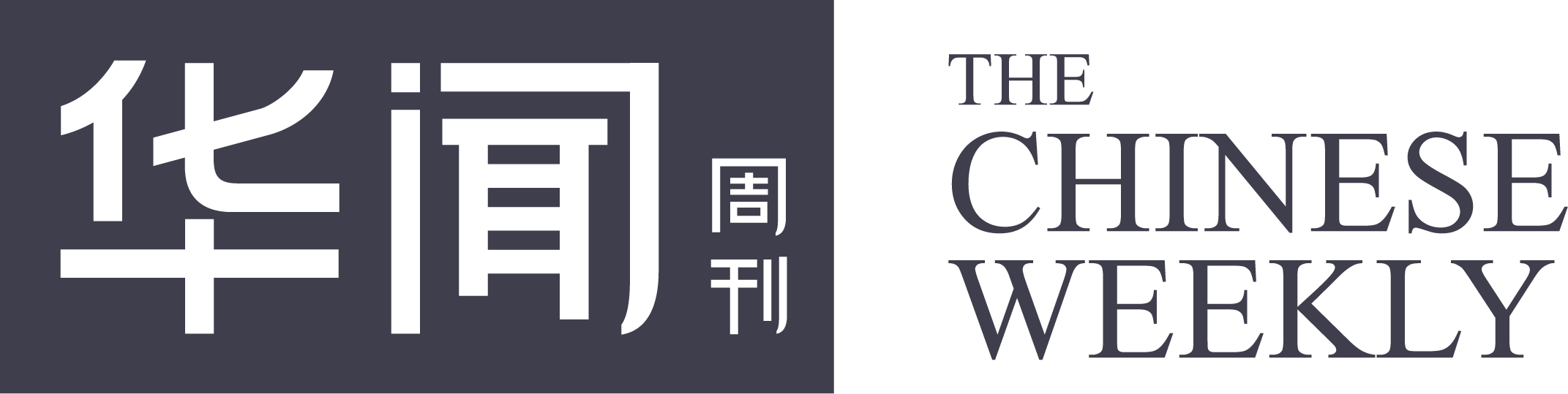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