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8日,我迎风走在他乡的海边,一深一浅地踩着微湿的泥土,冷冽的空气和静默的新树似乎在诉说着冬日漫长。而此时此刻,全世界人民都陆续进入了丁酉年,尽管这种纪年方式只有中华民族使用。在这个民族,过年的习俗也不尽相同,但通常认为“过年”是从腊月三十过渡到正月初一,意味着守岁、除旧、迎新。也在这个民族,过年已然成为镌刻在人们心中的一个符号,不仅生动地代表着压岁钱、团圆饭、贴春联、洗福禄、祭财神等等,更是真切地联系起许多人们即将淡去的记忆和回忆。
图:漫画家丰子恺笔下的“过年”
过年的时候说“过年”的意义,这个话题略显得有些无聊,但掐指一算,我离开这个符号的传统意义已有十年。过年,意味着一年又从指缝间溜走,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个时间单位在一生中占有如此大的比重,我想他们会恋恋不舍却又倍感无能为力;改变,悄无声息地发生,从无知到世故,从青涩到成熟,从无虑到牵挂,从期盼到畏惧。于是,在这些改变中,我们被放到许多地方、冠以各种角色、贴上不同标签。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年”对于每个人来说,既具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属性,又包含丰富的的社会学含义,值得我们品味和思考。
从物理角度讲,年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时间是一个不可控、不可逆的线性增长过程。正是因为时间的这些特性,人们只能被动地想办法描述和测量它,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如今多数国家使用元月一日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是来自于格莱格瑞安日历(Gregorian Calendar),这种做法在它之前的尤里安日历(Julian Calendar)和更早的罗马日历(Roman Calendar)就已经采用了。古人通过至点和分点的规律找到了这个时间点,作为新一个单位开始的参考值。中世纪的西欧,尽管当时尤里安日历已非常盛行,各国的君王仍使用各种不同月份作为新的一年的起点。时至今日,新年的计算方法已经基本统一,但还有不少民族和宗教采用特有的历法。比如,中华民族的祖先将纪年法和春分农耕巧妙地联系起来,这种方法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色,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韩国、以色列和印度等国家也在特有历法规定的时间庆祝新年。年,是一个人们历经千年、持之以恒地追寻却没能完全解开的迷。
除了时间计量,年更是一个所有民族共同庆祝的节日,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里有许多与这个节日有关的故事。比如中华民国时期,政府曾想用格莱格瑞安日历完全代替农历,遭到普遍的抵触。又比如,1914年圣诞节前到新年的节日时间里,一次世界大战战事胶着,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军人们实行圣诞节休战(Christmas Truce),势如水火的对垒双方聚到一处,交换食物和战俘,一起踢球甚至唱颂歌。过年,长长的书卷被展开去记录那许许多多的故事,以此承载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记忆,或喧嚣或孤独,或欢畅或忧伤。“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将自己置身于时空交错中思考“过年”,让我天马行空地想起许多与过年有关的记忆。
图:漫画家丰子恺笔下的“过年”
很小的时候,年对我来说是一种期盼,在那深冬时节,雪花飘飞的小村庄在我脑海里模糊又清晰。这种期盼一方面源自于对家和亲人的思念,因为忙碌的父母经常把我送去农村的奶奶家过年,甚至他们有时要到年后才能过来庆祝节日或者接我回家。于是,我有时会无奈地期盼新年快点过去,仿佛自己有永远用不完的时间。当然,在这个小村庄里,也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我曾经自不量力地站在略高处为长辈们讲刚刚听过的评书段子,也曾经无忧无虑地穿梭于每一个好玩的角落而且对大自然有足够的好奇心。当时对年的期盼另一方面源自于过年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大人们从各个地方将年货和礼品带到小村庄,他们团团围住灶台忙里忙外,然后餐桌上便升腾起浓厚的年的味道。吃过美食和放过鞭炮后,我和其他孩子满足地、似懂非懂地开始看春节晚会,不需要思考自己父母带来的礼品和其他长辈带来的相比,是多是少,是好是坏。
再大了一些,年对我来说意味着求知。从前的无忧无虑悄然地消失了,不再关心饭桌上的粮食和树林里的昆虫,我要为前途考虑更多,身上贴上了“成绩好的乖孩子”的标签。这个标签,有时让我沾沾自喜差点忘乎所以,有时也会让我倍感压力以致放弃坚持。也在那个时候,渐渐觉得自己强大地卑微着,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过年时,我盼望和从大城市回来的长辈交流,了解那里的故事和他们的生活,也时常为能抓起他们带来的“杂书”而兴高采烈。我喜欢和叔叔们走在积雪微滑的路面上,胳膊下夹着去串门要带的礼物,小心翼翼地迈步但并不畏惧可能跌倒在路上,感觉自己既是个孩子又是个大人,想要尽力装出并不底气十足的自信和洒脱。长辈们夸我又进步了,我嘴上谦虚,心里开心—浑然不觉那个标签便在身上贴得更加结实了,自己也和儿时对年的“期盼”说了再见。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一个人受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即便那时的我并不知道长辈们描述的“大城市”其实并不大,他们在那里的生活也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光鲜。
上大学以后,年是我卸下现实的家园。大学毕业时,我曾深情地写下一篇文章诉说即将离别时自己是多么不舍。然而,在自己印象里觉得还要在这个校园生活很久的前几年里,每到过年我就急切地想回家,带着自己汲汲营营地追求一个又一个目标后的一身疲惫和几分失望。在那个时候,我身上又贴上了名牌大学学生的标签,靠过年来“求知”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返,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我总在满是离愁的出发前夜才意识到,辛辛苦苦背回来的半箱子书还没有动过。过年时间里走到的地方,时常有人夸赞,也有很多羡慕的目光,可是我很少觉得自己有多么高大,只想卸去那一身疲惫和隐藏那几分失望。最享受的时光还是和高中同学相聚,大家倾诉着在不同地方的生活感悟,仿佛在时空隔绝之后,旧日的情感还存留在那个略微拥挤喧嚣的、曾流下过许多汗水的教室。酒足饭饱后,大家一同走在同样积雪微滑的路面,豪情万丈地回忆往昔、笑谈今日、展望未来—在那挥手道别的瞬间,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没法再回去体会从前的年味。过完年回学校,40多个小时的火车已经习以为常,车厢里的拥挤和音乐是那么熟悉,以至于今天我再听到那样的乐曲,就会觉得自己是踏上归途,仿佛新年已经悄悄临近。
发达的现代通讯,似乎让人们跨越了时空的阻隔,即便远隔千里,情人们可以传达爱意、互诉衷肠,亲人们可以彼此关怀、嘘寒问暖,朋友们可以互相鼓励、宽慰支持。微信语音可以随时发出,朋友圈信息可以极速传播—可是,这些都无法替代我心中的过年。假如今年我能回家过年,老家的小村庄在雪中依旧模糊而清晰,积雪的路面仍旧微滑,而我却再也没法穿越时空去过一个充满期盼和好奇的年。此时,我身上又贴上了“成功人士”的标签,也许会有更多羡慕的目光,人们依旧看不出我装饰和隐藏的一身疲惫和几分失望。置身于这些世俗场景,我不想再思考自己的高大与渺小、成败与得失、欣乐与哀愁、洒脱与牵绊—只想转身,望向儿时希望新年快过去好能相见的父母,盼望从他们脸上找到宽慰和微笑。
社会学里对于人的定义是各种社会角色的总和,随着成长,每个人都会有各种角色,儿女、父母、老师、学生、同事等等。岁月流逝,角色的交织和生活的轨迹给我们贴上了各种标签,夸赞的或奚落的,喜见的或无奈的。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寻求改变,开启新的生活方式;或关注常识并热爱这个世界,或接接地气并关心世俗生活;或告别颓唐并脚踏实地拼搏,或拥抱内心并放慢行走的脚步。可是你看,时间不可控也不可逆,我们没法复制一个曾经跨过的新年。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地过好每一个年,让它成为特定角色和标签下值得回味的新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新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雪花飘飞、模糊又清晰的故乡。
 | 王宏伟剑桥大学博士,在英国学习工作近10年,专业方向为国际工程设计学和工程信息学,担任多个高校兼任/兼职教授。工作之余,也热心社团工作,目前是英国浙江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委员,曾担任剑桥学联主席、全英学联副主席及英国浙大校友会执行会长。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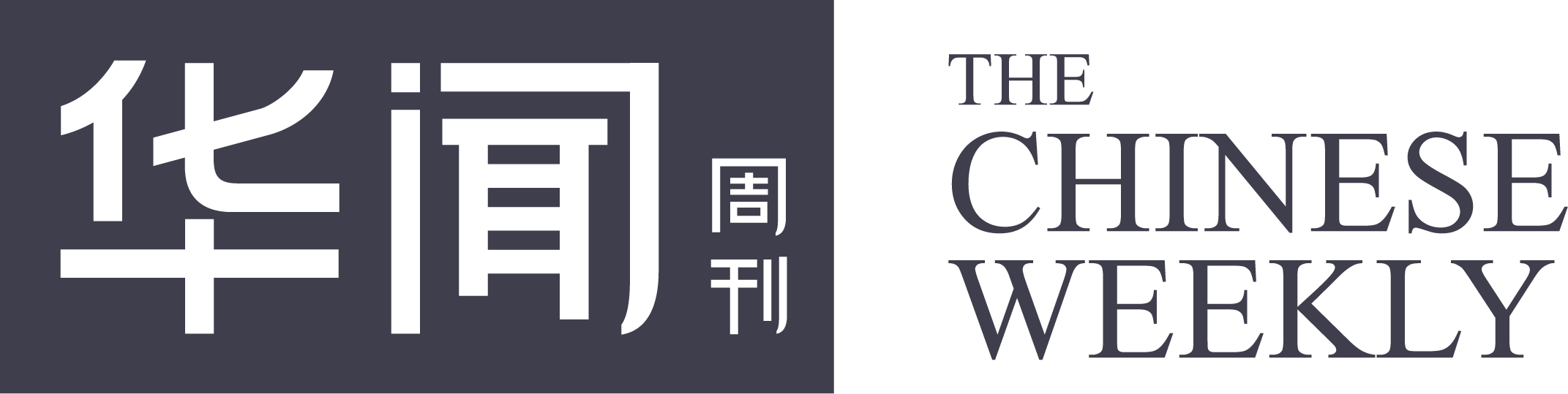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