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Sian Butcher / BuzzFeed
“那些尸体残骸从还有完整人形的,到缺胳膊少腿的,还有的就只剩下躯干了。然后我们就得对那些细小的组织碎片进行鉴定。验尸官说只要超过两平方英寸的碎片我们都需要进行鉴定。但问题是,残骸里有很多杂物,比如说可能是人们吃剩的鸡骨头,或者是死掉的老鼠,又或者是被撞死的鸽子。所以,在停尸房里也有一些人类学家,他们把肉从骨头上剥离下来以检验它们是不是人体组织。”
卡拉·瓦伦丁回忆着她在伦敦地铁爆炸案之后在临时停尸房里的工作,十年前她还是一位解剖病理学在读技师,也就是一位殓房助理。7/7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的时候,她不在伦敦,而是在利物浦的一间尸检室里清洗验尸工具,听着广播里的新闻播报,突如其来的伦敦地铁爆炸报道简直令她难以置信。地铁关闭、巴士停运,手机也失去了信号,整个伦敦都陷入悲伤与混乱中。
▲ 7·7爆炸案后伦敦陷入混乱
图片来源:Gareth Cattermole/Getty Images
第一次爆炸的二十四小时后,一间为接纳52名遇难者的临时停尸房已经建好。随着白色的大帐篷在英国荣誉炮兵连的花园上展开,伦敦城里的医院也准备好了1200张床位,等待着陆续送来的伤者。瓦伦丁在那个夏天刚刚完成她第二年课程的考试,周四爆炸案之后,周六她就被分配到临时停尸房里工作。
对于这段经历,瓦伦丁同所有人一样也会情绪激动,但是她的工作要求她更加专业和冷静。也因此她能诉说很多并不为人所知的事情,或者媒体发言人永远不会告诉你的事情。这些细节你不会在的士的收音机里听到,但这些细节会让你立刻感受到当时沉重的窒息感,比如文章开头那段记述。
处理爆炸遇难者遗体的过程基本都是一样的:瓦伦丁这些助理们要对接收来的尸体进行两到三次X光检测,找出隐藏的炸弹残骸,以保证在验尸官们把手伸进这些尸体里不会发生任何本可避免的伤害。他们需要配合SO13(警视厅防恐部门)和DVI(国际刑警组织灾难受害者识别)人员检查所有衣物和口袋,寻找任何能与之后的DNA检验相证实的物件。基本上,一具尸体平均会被十个左右相关人员围着,还包括两名助理和一名病理学家。尸体基本要经过证据搜寻检查,清洗,记录其他偶然发现的尸检(比如癌症),重塑,然后才会返回给其家属。
▲图片来源:Sian Butcher / BuzzFeed
停尸房的工作是有组织的,但同时也是混乱的——一群东奔西忙的犯罪现场调查员、验尸官,还有与家属沟通的热线接线员。在混乱中,瓦伦丁不断接收着尸体,同时也等待着更多的尸体被送来。
她自然也忘不了当时停尸房里送来的爆炸案犯的尸体。“我记忆里他们几乎没有一具尸体是完整的。我只能想象着他们可能的样子——年轻的生命,穿着T恤。没有任何特征可以把他们和别人区分开来。”在那特殊的一天,停尸房是安静的,只有悉悉索索的耳语,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爆炸案犯将被送进来。但当他们被送来后,并没有人对他们尸体的态度与对待其他人的有所不同。“最终来说,每个人在死亡面前都是平等的,”瓦伦丁说,“这些人也应当得到同样的尸检对待。那时候也有公开反对的声音,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为这些人建一个独立的停尸间吗?”
▲ 7·7爆炸案后临时搭建的停尸房
图片来源:Stefan Rousseau/ AP Photo
通常情况下,停尸房的生活是可预见的并且十分安静的,只有当活的生命进入时一切才会变得困难和不同。瓦伦丁打趣说,她成为验尸官是有原因的,因为她在面对活人时反而不太顺利。面对死者家属并安排参观停尸房是这份工作最困难的部分之一,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忍受。在瓦伦丁工作的停尸房里,工作人员经常难以向遇难者家属们解释他们将会看到什么,并且对于他们的工作来说根本没有帮助。
“我们得告诉那些家属们,他们是认不出他们的亲友的,并且也不值得这么做,我们会尽量阻止他们来参观。”瓦伦丁表示有时候只能无奈地告知,“但是如果他们坚持,我们会要求他们签一份弃权声明书,基本是说如果他们因参观而受到任何创伤请不要控告我们。”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在停尸房里会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即使尸检助理们已经使用了一些技巧让死者看起来不那么可怕:比如眼皮底下需要垫上棉球使眼眶看起来饱满一点,或让死者的嘴能保持闭合。
▲ 7·7爆炸案十周年,悼念者为已逝的亲属们默哀
图片来源:Peter Macdiarmid / Getty Images
在7/7爆炸案中,悲伤辅导顾问们开会决定遇难者家属们应当看到他们已故的亲人。尸检助理们通常并不会在安排家属认领尸体时为亡者上妆,因为那一般是葬礼时的事情,但这次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有些尸体实在已经支离破碎得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一些尸检助理开始担任家属来访顾问,那些极度悲痛的家属反映也不令人意外:恐惧、无法置信,甚至拒绝接受亲人的死亡。瓦伦丁只记得那些人喊叫着“不!这不是他!”,甚至在认尸房里撞翻尸体。有一位为尸体进行整理的助理还因为精神崩溃而被迫离开了。
“我们基本不被允许穿着医用手术服走出停尸房或者在草地上行走,因为电视镜头一直在拍摄,”瓦伦丁回忆道,“如果被他们看到我们穿着它,这或多或少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即使医生总是穿着它。”在手术服外面,尸检助理们都穿戴着手术帽和塑料围裙,所以并没有他们所担心的血迹——事实上,人们更为恐惧的是死亡的事实。
这次停尸房的经历并没有改变瓦伦丁出行的方式,甚至还成为促使她一年后从利物浦搬到伦敦的动机,在那次事件中她遇见了许多人。停尸房工作让瓦伦丁明白更多,她说,“我只是希望感觉自己是有用的。我不想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员,那些只会坐在电视前面然后抱怨,‘这太恐怖了!我现在开始不敢坐地铁了。’我希望真的做些什么去提供帮助。能够参与到一些重要事件并成为其中一部分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如果需要,我还会再去做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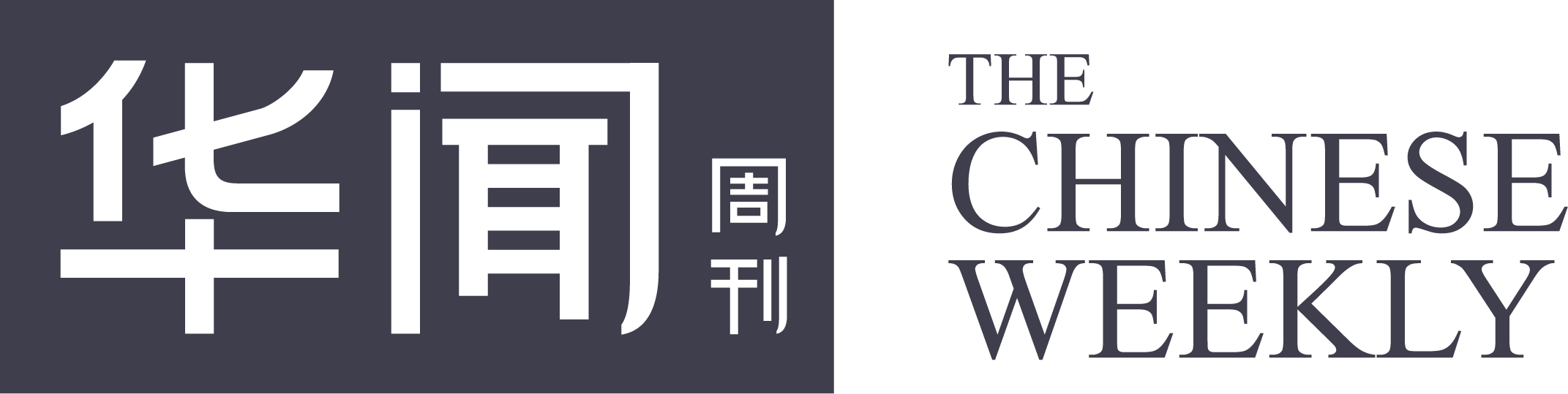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