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片被遗忘的原野上,苍凉的风笛阵阵撩拨着发凉的空气。在这里,尘世的芜杂仿佛都消失不见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成功突破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文化趋同之后,勇敢地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这样一群热烈的爱尔兰人,跳起这样一支欢快的舞蹈,最后这个沉睡的民族从音乐中苏醒过来,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在舞蹈中复活。在神话、传说及历史混合的极具纵深感的大背景之下,如泣如诉的爱情,波澜壮阔的战争,还有永恒不死的自由,构成了一部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大河之舞》。
作为一部叙述爱尔兰祖先们与大自然抗争、经历了战争和饥荒的磨难之后纷纷流离失所,最终回来重建家园的长篇血泪史诗,《大河之舞》绝对是爱尔兰民族的骄傲。这条大河里流淌着、传承着的,是爱尔兰人民的智慧、勇气与热爱,是爱尔兰民族的魂。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世界文化融合,使得《大河之舞》不仅在爱尔兰,也在全世界创下了居高不下的票房纪录,成为最经久不衰的经典音乐剧之一。而这悠扬的爱尔兰风笛,从1994年吹响的那一刻起,便不眠不休地响过了二十年春秋。
二十年前,百老汇超级制作人莫亚·多合第(Moya Doherty)在1994年的欧洲电视歌唱比赛中,特别制作了一个7分钟的舞蹈短片,在当时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于是莫亚便联合了麦克·弗莱利、作曲家比尔·惠南(Bill Whelan)和名导约翰·麦根(John McColgan)共同策划制作了在充实了原始舞蹈短片版本的构架之后的歌舞作品《大河之舞》。《大河之舞》之中,除了传统的爱尔兰踢踏舞之外,还融合了西班牙的弗朗明哥舞、俄罗斯的芭蕾舞以及美国纽约风格的爵士踢踏舞等其他舞种。
为了探究《大河之舞》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大艺术评论人一致推崇,并受到全球观众如潮好评的原因,《华闻周刊》对《大河之舞》的高级执行制作人朱利安·尔斯金(Julian Erskine)和领舞帕德瑞克·莫伊勒斯(Padriac Moyles)进行了专访。

(朱利安·尔斯金Julian Erskine,《大河之舞》高级执行制作人。有着近40年的文化产业从业经历,在职业生涯之初从事舞台管理、灯光设计和制作管理的工作,并建立了爱尔兰第一家专业舞台布景公司。1994年加入《大河之舞》团队,1995年起担任执行制作人至今,负责“大河之舞”所有旗下公司的管理和制片。)
今年,《大河之舞》有两个团队分别在英国、瑞士以及中国地区巡演。在中国地区的巡演中,《大河之舞》团队破例加入了特别的中国元素——在120分钟的演出中加入了约1分钟的中国音乐,《康定情歌》和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我们收到了中国观众的热烈反响,不得不说效果真的非常好,歌曲融合做得很棒。”朱利安很兴奋地对我说道。
要知道,《大河之舞》自2000年以来,便停止了对自我的修正和改变,“前期一直在不断地融合其他的舞种,经过了6年的不断完善,我们觉得已经趋于成熟了,而且观众希望看到稳定的演出内容。”朱利安如是说。“那为什么这一次要特别加入中国元素?”“想给中国观众一个惊喜。中国的音乐舞蹈也有着历史悠久的传承,将这两首歌曲加进去非常适合。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去展示自己的文化,也希望能参与到中国的文化中去。”
“那之后有计划在他国巡演时加进他们的民族元素吗?”我很好奇。朱利安却坦承说:“暂时还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做融合的时候会很谨慎,只有将这个剧变得更好的元素,我们才会考虑。而其实前期融合不同国家和地区音乐舞蹈元素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尽管如此,朱利安却颇为激动地告诉我,他们有计划在接下来的中国巡演中加入更多中国元素,比如明年沿着黄河两岸城市举办的“黄河之舞”巡演,“我们想回馈中国观众,他们对我们真的很友善。”

(帕德瑞克·莫伊勒斯Padriac Moyles,《大河之舞》领舞、副导演。1997年加入《大河之舞》,1999年成为领舞,斩获许多世界级爱尔兰舞蹈比赛冠军。2013年起开始担任《大河之舞》副导演。)
有过很多次中国巡演经历并刚从中国站巡演回来的帕德瑞克也显得异乎寻常地兴奋。他一直在强调他有多爱中国,即使很多时候语言障碍对他是一种挑战。“我绝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你可以去问任何一个人,我在说起中国的时候有多么津津有味。去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挑战,因为很难找到西方食物,我开始爱上了饺子、面条和各种美食。”
同时,他也告诉我,不同的受众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回应这个剧,比如中国观众喜欢用相机记录这个剧,希望能带回家去反复看,“我有时真的很希望他们能坐下来静静享受当下的音乐和舞蹈,不要去担心录像的事。”帕德瑞克还特别强调,“中国人的友好让我想起家乡的亲人,虽然有很大的语言障碍,我依旧非常期望同他们交谈。”
谈到《大河之舞》在中国大受欢迎的原因,朱利安肯定地说道:“他们欣赏舞者们的天赋和努力,因为中国人非常钦佩努力的人。还有他们很享受音乐,因为哪怕在只有音乐、没有舞蹈的时候我们都能收到非常好的反馈。”说起音乐,他坦言,这是他认为《大河之舞》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重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音乐和编舞的完美结合,为它赢来了全世界的观众。”他也透露,哪怕听音乐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二十年过去,他依旧能坐在家里安静地享受聆听的惬意。“比尔·惠南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他的编曲给《大河之舞》注入了血液。”而在编舞上,
“强大得令人激动不已”,这无疑使得这支舞台剧更加让人欲罢不能。
《大河之舞》的第一部分讲述了爱尔兰先民们的习俗和信仰,他们信仰太阳、月亮和星辰,信仰雨水、河流和风,强调尊重自然;第二部分主要讲述的是移民故事,人们去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开创他们的新生活,和其他族群交流、融合;第三部分是描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移民们回来改变留在祖国的爱尔兰人的图景。离开、归来、改变,这听起来就是生命最珍贵的往还。“我们需要不惧改变。事实上,往往有更好的方式去达成一件事。更具包容性,更开放地接纳他人,我们也能成为更好的人。”我看见朱利安眼睛里闪烁着的希望。
说起当初团队决定融合不同民族音乐和舞蹈的原因,他解释说,“《大河之舞》故事本身就是在讲述爱尔兰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离开家园、移民到其他国家,最后回来重建家园的故事。在这个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爱尔兰人将自己的舞蹈和文化一同带去,和其他国家的人互相学习,这在我们的舞蹈中反映出来了。比如非洲和美洲的踢踏舞,就和爱尔兰踢踏舞有非常强的联系,因为非洲的人们作为奴隶、而爱尔兰人作为穷人在美洲的土地上相聚,他们互相切磋舞艺的过程加速了一种非常现代的爱尔兰舞蹈的诞生;加入俄罗斯芭蕾舞的元素,是因为作曲家比尔·惠南和东欧音乐人一起工作过;而弗朗明哥舞跟爱尔兰舞本身就有着很高程度的相似。我们希望不只展示爱尔兰舞蹈,也要展示全世界最优秀的舞蹈给观众。”此外,他们也会从全球各地找来擅长不同舞种的舞者,这些优秀的舞者们聚合在一起,也会有一些神奇的融合发生。他们对此所持的态度非常开放,包容似乎是《大河之舞》至关重要的主题。
作为一个在《大河之舞》团队呆了17年的舞者,帕德瑞克的父母在移民大潮中搬去了美国,他出于对民族舞蹈的热爱,毅然回到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我问他如何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重复跳同一段舞蹈却不感到厌烦,他很坚定地告诉我:“我真的很爱跳舞,每天都必须跳,会不停地挑战自己,尝试做得更好,我觉得自己能做得更好。”
在他看来,《大河之舞》是他们民族文化的骄傲。作为一个舞者,帕德瑞克希望通过他百分百投入的表演,让人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忘掉烦恼、压力和挑战,从音乐和舞蹈中得到快乐,受到启发。
在交谈中,他们告诉我,在巡演中,经常会有观众追到不同的城市就为了反复地观看他们的表演。我问他们是什么能让一个舞台剧如此经久不衰,他们都顿了顿,却又很迅速地回答了我。“主创团队的激情和创意从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褪,他们让一件又一件不可能的事发生,不断地在让这个剧变得更好。同时他们尊重那些有创意的人,不光是在创造一个剧,也在打造一个品牌。”帕德瑞克自豪地说。
而朱利安也从制片人的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让一个剧长寿的最关键因素是观众,如果观众不喜欢,你不能强迫他们去剧院,这也是生活里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很幸运能拥有这样‘给力’的观众。”朱利安已经在文化行业工作了40年,但在他看来,能参与到《大河之舞》的制作中,见证《大河之舞》的巨大成功,是一辈子只可能发生一次的幸运。

“你们究竟有什么成功秘诀?”我穷追不舍。
“我真的不知道,人们就是喜欢来看这个剧,喜欢它的舞蹈、它的音乐。”朱利安幽默地打趣着,却道出了很朴实的道理:“如果我们清楚地知道所有准确原因的话,就会创造出十个这样的剧了。但事实上,这是天赋、能力、时机和幸运共同作用的产物,他们必须缺一不可地出现在同一时间。如果《大河之舞》早出现5年,这样的成功不会发生,因为爱尔兰还没有准备好。正好是1994年这个时段,爱尔兰开始腾飞,开始变得自信,作为爱尔兰人我们很自豪。《大河之舞》就在这个时间点精准地抓住了这个情绪。迟5年也不行,我们会错过那难得的腾飞瞬间。”他朝我挤挤眼,“在绝对正确的时间抓住整个民族的情绪,‘天时地利人和’,那么没有人再能阻挡你。”
“但要记住,你控制不了那些成功的要素,去强制他们同时运行。你可以做到你的极致,但如果没有所有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成功也不会降临。不过幸运的是,你不知道什么将会发生,只有尽力做到最好,期待着属于你的时刻终将到来。”朱利安很认真地强调着。
“如果让你再去做一个别的剧,你认为不会像《大河之舞》那样成功?”我问朱利安。他盯着我的眼睛,“事实上,有趣的地方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有只能去不断地尝试。因为不尝试,什么都不会发生。也许还有另一个《大河之舞》等在那里,而我们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来。”
爱尔兰上世纪末的经济腾飞造就了《大河之舞》,而谈到爱尔兰当下的文化环境,朱利安则直言不讳:“作为一个小国家,我们拥有数量极其惊人的作家、剧作家和音乐人。但我们完全有能力比现在做得更好。对于一个文化艺术如此发达的国家,政府在文化产业投入的资金这么有限,这很悲哀。爱尔兰的文化艺术应该更‘强大’,现在的情况只是‘不错’而已,英国和美国的剧院比我们多得多。当年,《大河之舞》在爱尔兰反响很好,但在英国上演之后才开始闻名于世界。不过你得考虑到爱尔兰是个小国家,观剧人数规模不可能很大。我其实理解,政府如果只有一定数量的资金,的确应该更多地放在医疗、教育、食品等方面,但我坚信,艺术是我们的根,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自己是谁。文学、音乐、舞蹈和讲故事的方式,构成了爱尔兰人,我们必须确保这些东西不被遗忘,这也正是《大河之舞》的精神所在。《大河之舞》尊重我们民族的传统和起源,它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舞台剧而已。”
帕德瑞克也印证了朱利安的话:“我们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每个爱尔兰人都为《大河之舞》属于我们自己而感到自豪,每个人都愿意用积极礼貌的方式去向别人推荐它。”
整个采访下来,我被无数次震撼到,尽管从没有在爱尔兰生活过,在面对这两双坚定的爱尔兰眼睛时,我心里还是充盈着感动。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在击打着我的思维。我不得不承认,这些勇敢、肯吃苦的爱尔兰人,让我发自内心地倾慕和敬佩。
由此即彼,我们聊起我的祖国,朱利安坦承了他的看法:“我很惊讶中国没有一个现代导演来做一个像《大河之舞》这样的现代舞蹈秀。
20年前,我们开始制作《大河之舞》,这被看作是革命性的举动。有人甚至批评我们的舞蹈秀在爱尔兰舞蹈上处理得非常糟糕,因为我们改动了爱尔兰舞蹈而并没有保存它的原貌。但我认为每一种文化都需要被刷新,需要被更年轻的一代接受。因为有些传统的东西如果一直不变,会变得很无趣。很多人是因为《大河之舞》的出现,才开始重新关注爱尔兰舞蹈。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需要一支《大河之舞》,很期待有朝一日能欣赏到来自中国的这样的作品。”我不禁连连点头。
作为爱尔兰人,帕德瑞克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关注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大河之舞》塑造了我的性格,我很希望能够参与到塑造《大河之舞》的过程中来。以前跳舞只能看到作为舞者的那个方面,而现在我更想看到全局,试图去对一个剧负责,做出更准确的决定。”这也是为什么帕德瑞克现在多了一个“副导演”头衔的原因。“我想去帮助指导和教授爱尔兰年轻的下一代,他们应当更加有创造力和有担当,民族的未来在他们身上。”我想说,他多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头衔而已。
帕德瑞克的女儿刚刚降生,在他兴奋和充满感激的讲述中,我看到的是,这条大河,在孕育着一代又一代新生命的同时,也孕育着爱尔兰民族的希望和荣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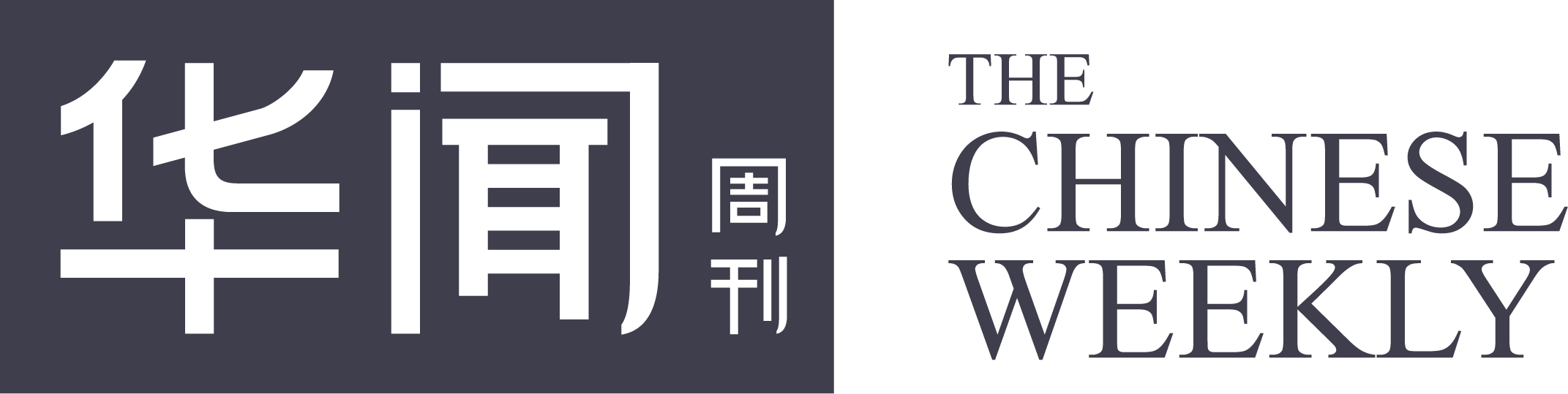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