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出无对白的实验性戏剧,道具简单到只有5把椅子,演员们全靠肢体来展现自己的内心情感,试图通过视觉、触觉、听觉在身体的内部寻找出口。如同英国著名画家弗朗西斯·培根作品中的人物,充满歇斯底里、躁动不安的气质,企图在不断地毁灭和重建中寻找自我存在感。爱情或是欲望?保护还是占有?《Normal Love》抛给了观众一连串的问题。

周日一早,十多个年轻人来到伦敦市中心Cockpit Theatre的排练厅,准备《Normal Love》演出前最后一天的正式排练。在二楼的排练厅里,该剧制作人杨佳静向记者一一介绍了《Normal Love》的所有成员。有趣的是,这部戏虽然选用了4位西方演员和2位演奏家,但核心主创却全是华人。
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讲述爱的不同关系和不同体现。当女演员和四个男演员并排坐在舞台中央时,女主角更像是一个提线木偶的操控者。观众不难发现,有的男演员头发上绑着一根线,而有的男演员手腕上绑着一根线,唯有一个男演员身上没有一根线,但他仍被女主角牵扯着。导演凌子说:“我喜欢研究现实主义的东西,现实主义和荒诞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回事。在这种虚与实之间,你看到的就一定是真实的吗?就像你看到有些完美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里面支离破碎到什么程度,谁知道呢。”
或许是与过去只需一个人思考的绘画经验不同,凌子也在不停地转换着她在纯美术和舞台剧之间的角色转换。但她仍拒绝用眼睛去看世界,而是用某种质询和怀疑的世界观去看周围的人和事物,也包括自己。
这部戏表面上呈现了男女之间的关系,但抹去性别和很多其它的元素,它强调的却是更加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凌子介绍:“用女性身体和男性身体的对比给观众造成一种错觉。我想打破观众惯常的观剧方式和原有的理解。观众看到的好像是一位女性和一群男性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这个戏说的是一群人之间的关系。”
今年初,当凌子决定要做这样一出舞台剧时,还只是一个不具体的概念。她找来了服装设计师赵彤、舞美设计师王晶和灯光设计师谭华,最后她们都成为了《Normal Love》初创团队成员。
“最初和凌子聊天,我们谈到用简单又细腻的肢体来做方式表达,展现复杂情感中痛苦挣扎的黑暗感,于是我们用线贯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想法才慢慢清晰。”谭华回忆着与凌子讨论《Normal Love》的初衷。作为灯光师,谭华将整部剧的灯光设定为冷白调,创造出不安的空间感和被压缩的平面感。
有了“线”的概念,赵彤就开始利用这一点为演员们设计服装。“有一件衣服特别有意思,女主角穿的一个四件套都是用线连着的,用来表现一个穿着很好看的女生站在那里,而其他几个男生过来撕扯她,就像强奸一样,拽断一根线,一件衣服就像一滩水似的从身体上滑落到地上。我们表达的就是‘线’或者人与人之间的脆弱关系,抽掉它,一切就全垮了,就像人类之间的爱一样。”
而王晶曾因创作理念上的偏差与凌子有过争论,经过了半年的磨合,大家也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契合点:“与凌子的这次合作,和过去我在职业剧院的工作经历很不一样。这部戏创作之初没有剧本,只有Normal Love这个主题。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创作时会有冲突和磨合。在进行了四稿舞台设计方案之后,我找到了她想要表达的东西。”
专访《Normal Love》导演凌子
《华闻》:为什么会利用肢体来表现戏剧?
凌子:我不爱说话,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我希望我们能用眼神、感觉交流,能懂对方。我朋友不是特别多,以前做美术绘画可以不说话,可以待在自己房间里做自己的事情。然而做戏剧就不同,全是人的事情,可我还是不想说话。我喜欢舞蹈,但又不喜欢舞蹈的语言,舞蹈的语言对我来说太具象了。舞蹈的那种感觉太强烈、太张扬。我希望有一种语言,是我的语言,但通过身体表达。所以我把它建立在舞蹈和肢体剧之间,自然而然我就只能用肢体去表达了。
《华闻》:但女主角在演出时,还是有很多舞蹈成分,这是为什么呢?
凌子:舞蹈是一种肢体语言,女主角的这个舞蹈是随性的,没有编舞,表现的是一种非常开心的状态。我之前用过几个舞蹈演员,我发现舞蹈演员永远摆脱不了他们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一做我的东西他们动作非常大,非常有表现力,可是我不需要这样,我要他们本身的质感。我现在找的这个舞蹈演员就很好,她摆脱了舞者的一些东西,回归到了人本身,再加上她本身有肢体的训练,很有感觉,跟我吻合到了一起,我也没想到会和这个舞蹈演员配合得如此之默契。
《华闻》:我注意到有一个男演员头发上绑着一根线,被女主角牵着走,这个细节很有意思。
凌子:对,每个男演员都不一样。但其中一个被提起头发的不是男人,他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性别的人,因为他在爱情里没有自我。我研究的是关注和忽略之间辩证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话题。我一直认为,他因为完全只关注女主角,因此忘记自己的身体,忘记自己。而观众作为旁观者却可以跳出来,他们会看到大量的潜台词,我们给观众营造了一个对比的空间。因为他的“自我”的丢失,观众就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华闻》:这与你的个人经历有关吗?
凌子: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跟我的艺术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就是爱,这个爱包括各种形式,友情、爱情、亲情,包括与陌生人之间的感情。我觉得情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它本身也是一种材料,我在用它。我觉得我的艺术离不开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要挑选一种情绪的东西,那么这种情绪我选择的就是爱,用这种非常广又非常小的东西去做。爱的各种语言、各种声音,所有人都能理解,但它又是最难理解、最深的东西。我想把它挖出来,用生活中最普通的材料跟它联系在一起,去挖出一场戏,用自己的经验挖出爱的一个角落,告诉观众我认为这个爱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我希望大家有同感,或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我希望找到人性里共同的点去把这个爱挖掘出来。我成立的剧团就叫Normal Love,也就是说我的每场戏都跟爱有关,我会做不同角度跟爱有关的东西去诠释它。
《华闻》:创作这部剧的灵感来自于哪里,为什么会想到用一根线穿插整部剧来表现纠葛的内心世界?
凌子:创作故事之前,我知道自己内心充满能量,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找到一个出口去表达。就是说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这是一个疑问。我属于意识流派,完全跟着感觉走。我以前画画,可以用一根线画出一幅作品。我这次想要找到一个材料,然后通过这个材料属性去研发出一个作品。但我很清楚,我的理念一定是离生活非常近的东西。我用香蕉、雨伞等做过艺术实验,最后都觉得有点重、有点大,一直没找到这个东西。直到有一天在家里,和我合住的朋友是做服装设计的,她的线引起了我的注意,突然觉得我要用它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拿去工作坊让演员试,一试就试出感觉了。
《华闻》:剧中只有一个女性角色,会影响挖掘真实性的东西吗?
凌子:我所追求的是现实主义。虽然只有一个女性角色,可是我需要的是女人的身体,她本身是不是女人其实不重要。我在戏里着重想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想把这种关系抽离出来,把其它东西像身份、性别这些东西尽量都抹去,但我保留了演员本身的一些东西。就像其中一个演员他很明显就是一个Gay,我开始想要不要去掉这种扭扭捏捏的元素,后来想没有关系,这样又多了一个人的层次,我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给一个女性的角色是为了在视觉上打破平衡。我做的所有东西首先要有视觉感,因为视觉可以让你理解很多直观的东西,比如一个很破的手机、很破的鞋和一双新鞋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它的故事就出来了。我虽然在剧中用了一个女人的身体,但并不强调她是一个女性。

《华闻》:演出最后大提琴演奏者拉琴时离开琴弦,在琴身上拉,是想传达什么呢?
凌子:那个大提琴就像一个女人的身体,这部戏有一部分来源于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我感兴趣于他的暴力和色情。我里面有一些色情和暴力的元素,这是人最基本的感情。比如他对大提琴的感觉象征他对女人的态度。整部戏女性主义色彩比较强,女生本来是很占有主控权的,但你会看到男生后来把她衣服一件件抽掉,撕裂掉。这是为了让作品达到一种平衡,不想让女性主义表现得太激烈。
《华闻》:当你在创作一个作品时,你用什么文化基础在思考?
凌子:我觉得我是用一种东方的视角,西方的思维在做这个事情,正好反过来了。我以前做的平面作品,老师会说你的画不像中国人画的,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那么过来之后我开始理解我的东西,我的东西不是东方的或西方的,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有些东西既有西方心理学的东西,又有亚洲哲学的精神,东方的精神。所以我的东西不是什么民族的,东方的或者西方的。
《华闻》:在这出舞台剧中,导演和制片是中国人,而演员基本都是西方人,这种创作方式里会不会有冲突?
凌子:当然有冲突,有冲突才会有刺激。首先这里有很多种不同冲突,演员来自不同的国家。语言就是一个有意思的点,演员背景都不一样,有学Performance、Acting、Dance和Physical Theatre的,这些都是微妙的区别,他们本身专业的语言都不一样,表现方式不一样,那么冲突就来了。我有个演员学Acting同时还学哲学,我很多时候对那种未知的东西非常感兴趣,比如今天我们要用叉子做一个东西,至于做什么我不在乎,就是顺着感觉走,因为我有感觉要做到什么程度。演员很难接受这种方式,他们不明白要做什么。但对于这种即兴的东西,我特别不喜欢告诉他们具体要做什么,这是我们之间强大的冲突。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佳静,她做过导演,本身对艺术又特别有感觉,在排练一半的时候她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开始做沟通。比如,一开始做工作坊时,我希望状态是很开心的,后来问题出现了,我真是没办法交流,是佳静帮我去和演员解开这个结的。
《华闻》:这次是你第一次做导演。杨佳静曾经导过一些戏剧,这次是制作人,她对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凌子:最多的话?太贵了!哈哈,她总说太贵了。和佳静合作,最大的帮助是我学会了省钱。我之前做艺术的时候,没有想过现实的问题,完全依照个人意愿在做这个东西。但佳静在用人和用钱方面对我很生气,因为我没有逻辑,乱付钱。艺术家可以任性,导演不可以任性,因为牵涉到很多人的关系。
导演简介:
凌子出生于艺术世家,父亲是中国著名油画家凌徽涛(85新潮美术运动倡导者之一)。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后保送到中央美术学院。2011年至2014年间留学于英国切尔西艺术学院和英国皇家中央演讲与戏剧学院,进修硕士学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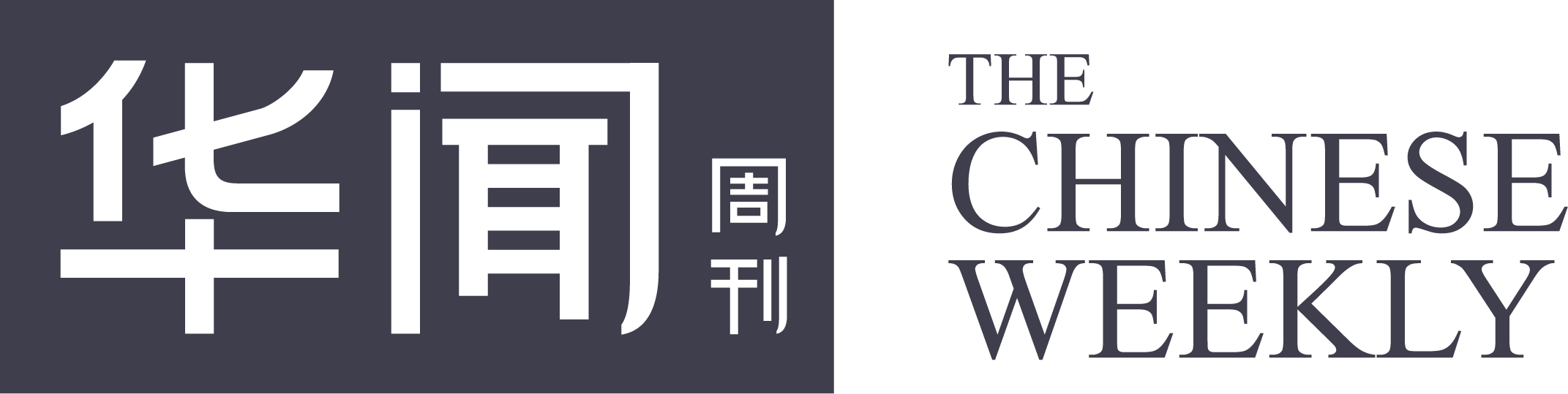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