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半夜起来,蓦然体会到夜凉如水的用意来。
中文还是在的。离开中国,是因为中文已经在心中,走遍全世界都能用它写小说。我跟我爸说要他把家里的《醒世姻缘传》寄过来——最近突然强烈想看古文。我爸说我妈从北京寄回家的两大箱书,他全部用纸封起来了,怕落灰。于是我作罢。
最近突然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压力的。在北京的同事们已经挤破头了在买房;来伦敦遇见的中国人,有的已经买房,还没有买房的或最大的心愿或谈论的还是买房。
在欧洲企业工作的最好一点是最起码身边同事不是都急着买房的人。昨晚一个葡萄牙小伙在泰晤士河的廊灯下对我说,他要自己盖一座房子,说是家族传统。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不像北京的。
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压力的。比如我现在不能像英国、欧洲同事那样享受生活,因为首先要解决工签问题。很难找,特别有压力。此时,我几乎觉得这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我们昨天去的那个酒吧我觉得很喜欢,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以前是码头边的那种阁楼,高高的建着,干干爽爽。我们选择了露天的位置,头顶是那种很高的穹顶,小巴黎的感觉。深度雕刻,旧水晶吊灯。然后可以俯视脚下的泰晤士河,不知名的霓虹灯在不远处的桥闪着,浮生若梦。
我们昨天午餐时在Canary Wharf地铁站前的那一片空地啃三文治。所有在那一块上班的上班族基本上都在那里午餐或下班后喝一杯。然后我的一个同事,指着我们面前的那座大楼对我说,那些二十多层楼的窗子后的穿西装的人,此时说不定正在望着我们这些为几千英镑薪水抱怨老板是怪物的人。而那些窗子后的人,一天就赚一百多万英镑什么的。“你想想,他们此刻俯视着我们。他们心中会想些什么呢?”
也许一百万英镑不是准确数字,因为我对数字实在没有概念。总之,我对钱一旦过多或过少以后就没有概念了。太多以后就觉得都是零。太少了,像每次买东西找我零钱,除非是整数。否则我也是不会算的。
Anyway。他说的那个对比我觉得很有趣。这就是云泥吧,而我们是蝼蚁。可是欧洲人的蝼蚁感是绝对没有万里之外来的中国人那么强的。
一个辞职的同事请我们每人喝了一杯龙舌兰酒。那还是我第一次喝。我还真的挺喜欢的,用他们的话说,喝完真的很refreshing(清新)。她有一个家庭要负累的。她说自己的财政也并不是很好。然而我就喜欢她那样的洒脱。为了自尊还是辞职,然后还大大方方的为我们每人买一杯龙舌兰酒。罗马尼亚人的洒脱。
中国人是很少辞职的。赖也要在某单位赖至退休。做生不如做熟。欧洲人的思维还是不想太委屈自己灵魂。然而我那一晚还是闷闷的。我还是像宝玉似的,喜聚不喜散。永远都慨叹散场的悲哀。像我大学主持完一场晚会看着满地狼藉无比难受。
此时已是九月下旬。工签悬而未决。这个东西真的横在我心,不知什么时候能解决或永远不会被解决。像《边城》的结尾。然而我喜欢《边城》的一切却最恨它的结尾。翠翠就那么在那条摆渡的船上永远等着,他也许明天会来,也许永远不会来,太傻。
此刻我开始深夜难眠。在黑暗中难以瞥见自身的前途以及明晰未来。有人说你是不是想留下来。我说,我不是想留下来,而是不想回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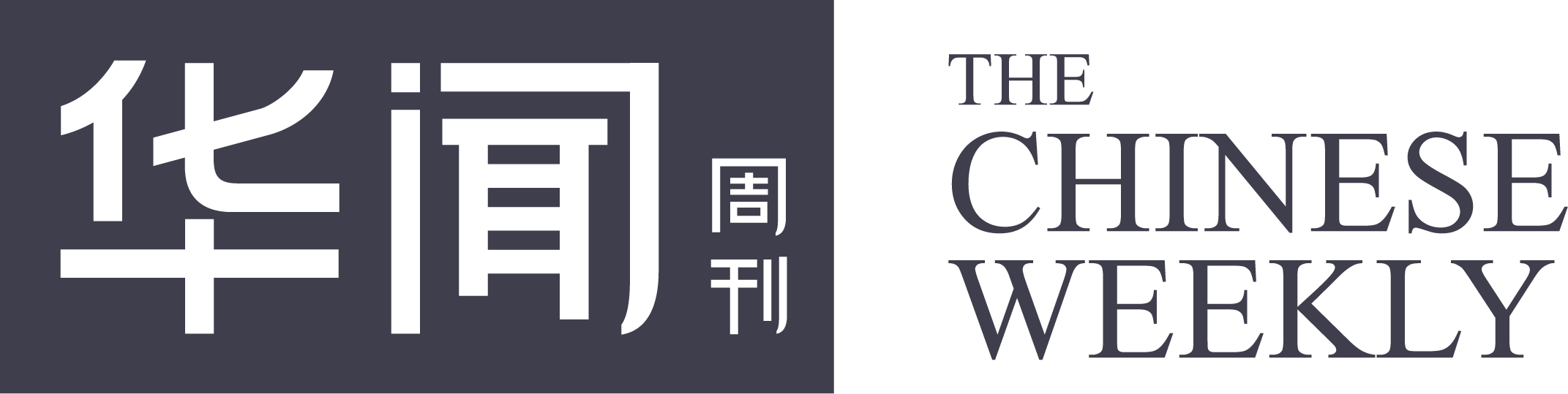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