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天注定》首映的夜晚,伦敦街头下起细细的冷雨,我从Gower Street步行到了位于唐人街的Odeon电影院。想着这电影,一路便回忆起贾樟柯之前的作品,这一程竟忘了打伞。牛毛雨看似无谓,却完全打湿了我,正如一位漂泊的诗人曾告诉我的:伦敦的冷雨就像悲伤,悄悄地浸透了你的脊梁。
我知道将要面对的 《天注定》是四个冰冷绝望的故事,取材于中国这几年发生的真实事件。第一次在异乡看一部表达中国社会现实的电影,排在长长的进场队伍中,我竟有陌生的恍惚。这是嘈杂的唐人街,山寨水煮鱼的味道远远飘来。一辆三轮车装着两个中东人飞驰而过,我的脑海中莫名奇妙响起贾樟柯的《世界》里那曲《乌兰巴托之夜》,可是,这是哪跟哪呢?戴着高帽子的英国警察背手走来,看着某餐厅橱窗里一只酱板鸭发呆。几个中国人聊着余姚的大水,说那里出现了骚乱。可是他们很快被对面著名的Gay吧引走了话题,热切地讨论着是否要进去一饱眼福。我感觉像回到了北京的三里屯,便躲去一个灯影下的角落,地上散乱扔着几份内容和印刷一样狗血的中文报纸,雨水泡散了油墨,把一则消息上的习总书记弄成了奥巴马。不远处那个中年妇女仍在控诉,每次来她都在,她可以旁若无人地喊上一天。有人说她是在工作,也有人说她有病,而我觉得不管是哪种,她都是个可怜的人。
电影开始了,王宝强绷着一幅冰冷面孔出场,令人颇觉诧异,仿佛他在欢天喜地的泰囧之后,被捉回苦大仇深的盲井关了半年。有三人持械劫道,本该是场轻松的小规模抢劫,这过年开摩托回家的“民工”却掏出枪来,四枪将他们搞定了。没有话,没有慌,没有迟疑,杀了这几位,“民工”三儿连口唾沫也懒得吐,他只是继续上路,还是原来的速度,还是原来的表情。他路过一起交通事故,姜武扮演的农民大海在一边无所事事抛着西红柿。镜头转向了大海的脸,于是,他的故事开始了。
姜武演的大海是我们在网上很熟悉的人。这个一根筋的农民活在毛主席塑像依然伫立的乡村,他有一肚子明确的愤怒和一副实在草包的皮囊,寄往中纪委的告状信都不知道写什么地址。面对狼狈为奸的煤老板和村委会,他生气而妒忌。他洞悉整件事肤浅的奥秘,却弄不懂为何全村人都没心没肺,愿意为一袋白面就去给煤老板坐台。他要把煤老板和村长告倒了,让村子应得的利益浮出水面。但他显然不会成功,对手是强大的,视他如同草芥;环境是麻木的,所有人都觉得他嘴多,连老相好都不让他摸手了,劝他先过好自己的日子。大海的“无事生非”终于招致一顿暴揍,被一柄铁铲打破了头。村民们漠然离去,还给他起了个新外号。可是,所有人都忽略了这个 “欠揍的多事者”之可怕之处,凶狠的对手或许会令他退缩,但那些来自村民的嘲笑和冷漠,终将他逼向尊严的死角,走上一条不归的灭绝之路。他扯去绷带,也扯去了屈辱,将双筒猎枪裹上一幅老虎年画,宛如一只羊穿上了威武的虎皮。会计杀了,会计的老婆杀了,喊他外号的人杀了,村长杀了,去杀煤老板的路上,他顺道把早就看不惯的那个虐待牲口的车夫也杀了。那个王八蛋只知道玩命抽鞭子,却不管他的马拉了多少沙子。煤老板想必悔之晚矣,他的脑浆冲出玛莎拉蒂的车窗,飞洒在泥土和煤灰之上,瞬间消失,连抹鲜红都看不到。枪声后的静默里,炼焦厂的烟囱冒着烟,阴霾覆盖着大地,村口戏台上唱着林冲雪夜上梁山。在大海的微笑中,那匹终获自由的马拉着车轻快地走起来,逆行于车流,在警笛声中渐行渐远,它义无反顾地走向自己想象的远方,不管那里有多么寒冷。
在电影结束后,我听到《华闻周刊》对一个英国人的采访,他对这一场戏非常费解,这就要杀人吗?要杀那么多人吗?政府呢?法律呢?不是也有警察吗?我对他的质疑并不奇怪。宽阔的长安街,宏大的奥运会,威武的阅兵式,不差钱的中国游客,欢乐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它们砌成巨大的迷墙,挡在世界和荒野之间。人类容易陷入符号和宣传的陷阱,说法国,我们便会想起埃菲尔铁塔;来英国,便会跑去伦敦眼和白金汉宫;去美国,谁会不知道自由女神呢?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真相都不在那些知名之地,而在大楼的阴影下和无名的乡村里,它们往往在火车道延伸而去的尽头,在应该平静舒缓的乡野,可是,中国的城里人们,你们了解自己满目疮痍的乡村吗?
“返乡民工”三儿回家了,全家人对他神憎鬼厌,他要捏哭了儿子,才勉强给一副死人脸的母亲鞠了躬。两位大哥来找他,没有任何寒暄,上来便亲兄弟明算账,他们将母亲的七十大寿刻意拖后,为的是能有更多返乡的亲戚送来红包。三儿冷冷看着大哥将那点儿他根本看不起的钱分干净,连公款买的最后九根烟都分干净,冠冕的公平之下,亲情分扯得一丝不挂。三儿沉默寡言,走串村民聚赌之处,看着他们无情互殴,只是冷冷一笑。他时常望着村子隔江的那一边,那里有一排排恢弘的高楼大厦。一江之隔的世界,将更多的苍白和不安留在这边。妻子洞悉了他杀人劫财的买卖,不解他为何非要离去。我本也不解,直到三儿说出“无聊”二字。年三十到了,他带着儿子来到江边,对岸升起绚烂的烟花,那繁华绚烂却虚幻,真实却又无力。三儿让儿子看他的壮举,那朝天一枪淹没在震天的烟花中,不闻声息,不见火光,却足以要命,并正在代代相传。这早已失去信仰和人性的乡村,面临城市那高调的进攻惊慌失措,充满无家可归的担忧,他们本能地反抗,或用冷冰的脸,或用杀人的枪。最为卑微的面孔之下,早已掀起最为深刻的残忍。那一枪是这个农村杀手对那花花世界的蔑视,是对儿子最为真实的言传。他早已知道,那貌似强大的对岸是毁灭这乡村“该有的生存”之罪魁祸首,是撕碎农村亲情的无耻之徒。他觉得每一个江那边的人或为帮凶,或为看客,没有一个是无辜。他不明白为何扣动板机的那一刻才感到自己的存在,只觉得江那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杀,因为你不杀他,他早晚会折磨死你,欺负死你,鄙视死你。这并非终极的仇恨,却是无法挽回的敌意。
是吗?不是吗?看到三儿再度杀人,再度离家,在大巴车电视里《放逐》的枪声中,他消失在黑暗的山野,消失在毫无所谓的途中。他来去无踪,漫无目的,他仍会默默杀人,要么致人死地,要么被人击毙。但他无法停下,因为他生长的那个山村,已经全然不是精神的家园,更非幸福的归宿。看到此刻,我被不可救药的恐惧袭卷,被带着惭愧的悲伤占据。我们掠夺农村的土地,摧毁农村人传承的信仰,打着城镇化的旗号将最为功利的哲学灌输给那些原本质朴的人。他们因此恐惧、伤心、麻木、无聊。当人生变成漫漫的白纸,注定画不出生命的原色,邪恶便会重回万物生长的大地,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悄然弥漫。每一个中国都来自于农村,也都毁于农村,中国的历史就在拯救和毁灭农村的轮回中周而复始。我们总在最不恰当的时候蔑视乡村卑微的存在,肆意践踏它的尊严,以为一袋白面便可以收买其中每一个粗鄙的灵魂。我们就是那个玩命抽着那匹马的野蛮车夫,拉着一文不值的财富,放弃曾经温善的良知。我们看不到那些绝望的双眼,不明白它们正在变成要命的双筒猎,那报复的一枪说不定便会在烟花绚烂的一天轮到你我。
在影片转去第三个故事之前,我想起在山东平度举着大刀抗拆的记者陈宝成。他坚持以法律手段与强拆他家老村之屋的对手抗争,纵然手持大刀,却没有伤一个人。政府以之为稳定大害,终于寻机将他捉了进去,不明不白地关了一个多月。这高调而守法的斗争,和三儿这个低调的杀人者构成巨大的反差。那些最具杀伤力的人往往沉默,那些真要杀人的人往往无声。大海是被逼上梁山的,三儿却是自我放逐的,而他们殊途同归,都成为这个时代最可怕的毁灭者。他们要干掉的不是哪个具体的仇人,而是我们这个不让尊严在阳光下存活的悲剧时代,他们会让我们毛骨悚然,他们就在你我身边。
因为辣椒吃的太狠,后面两个故事纵然芥末生猛,我却平静了很多。赵涛扮演的小玉,从一出来便挑明天注定的纠结命运。她在情感上的失落和桑拿房中的遭遇,不像前两个故事那般因果明确。因此它需要一个过渡,装着美女和蛇的表演车里,刚挨了一顿打的小玉和终日坐在毒蛇里的美女四目相对,无声交流。不必言说的共同命运,使她们顷刻便惺惺相惜。这场陌生的面对,虽然带着微笑,却比《世界》中安娜和赵小桃在夜总会洗手间的泪眼相拥更为苦涩。昏暗的灯光下,那些毒蛇盘在美女脚下,却钻进小玉痛苦的内心。这个世界,对她们来说就是这装满毒蛇的牢笼,一块钱可以旁观,一辈子无路可逃。当四眼嫖客举着一沓现金抽打着小玉最后的尊严,又出现车夫鞭打马的回响,弱女子变成了双筒猎枪,她只能选择挥刀相向,在自己想象的武侠幻觉中手刃对方。此时此刻,杀戮变成绚烂的花开,嘶吼成就弱者的悲鸣,面对一个嫖客充斥的江湖,要么忍受蹂躏,要么反戈相击,否则,还能怎么样呢?这个名叫“夜归人”的桑拿房,和那个蛇笼有什么区别呢?
影片最后,她逃到(也可能是无罪释放,这是该片暗存的善意可能)大海的村庄,脸上丝毫没有杀人者的忏悔。看到村口那几个眼袋耷拉的戏子唱起“苏三起解”,那连续三声“苏三,你可知罪?”也是她深深的自问,有罪吗?没罪吗?我们到底怎么了?他们到底怎么了?这个世界,又到底怎么了?
如果说前三个故事都与罪恶有关,最后这个则显得略加温暖。当东莞夜总会的小姐们穿着苏联军服、迈着正步出来接受嫖客的检阅,雄壮的苏联歌曲衬托起最为昭彰的淫荡。和这里五花八门的色情业相比,性都阿姆斯特丹的把戏只是情窦初开。而这里却发生了最为纯洁的爱情,打工仔小辉爱上了天天迈着正步卖身的妓女。这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雨中表白之后,小辉再无法忍受她钻进那台肮脏的色情列车,也无力将她救出这撕心裂肺的虎口。他没有决绝的胆魄走上大海、三儿和小玉的路,于是只能杀掉自己,摔成碎片,这一场无望的爱情便能永恒。他只能等待下一场转世与轮回。然而,在这没有救赎的世界,这些绝命的鸳鸯们转世不出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变不成邦妮和克莱德,或许他们只会转成一对天生杀人狂,转成愤怒的大海、无聊的杀手和怒吼的小玉。看到此时我不由疑问,这是贾樟柯的影片主旨所指吗?那些曾经的三峡好人们,只隔去几年光景,就步入必须血溅五步的深渊?
看了一些网上介绍后,我曾担心《天注定》是中国版的《通天塔》或者《撞车》,仿佛将《社交网络》山寨过来的《中国合伙人》。影片结束之后,我松了口气,它只是贾樟柯的《天注定》,它没有刻意穿插那些看似随意实则机巧的故事关联。贾樟柯这份“不向经典致敬”的勇敢,恰是藏拙于朴的自信。不懂中国本质的导演,断无法拍出这样的片子,而不懂自己的中国观众,也看不懂它想表达的深刻内涵。影片之外,大洋遥远,在我那欲望无止境膨胀的家国,在那些盛大的繁华之下,藏着随处可见的危机。一个十几亿人相互倾扎的中国,在文明的背面越走越远。天注定的命运之下,一个国家注定的命运昭然若揭。如果说贾樟柯的 《世界》预见了当年中国必将走向的精神荒芜,这一部《天注定》便给如今的中国打上了走投无路的时代标签。面对影片中这四个有进无退的匹夫,没有谁是无辜的,没有谁能置身事外,在那场必然的末日之前,在每一次义愤填膺之后,我们或更该在迷茫的星空下扪心自问,如何救救他们,如何救救我们自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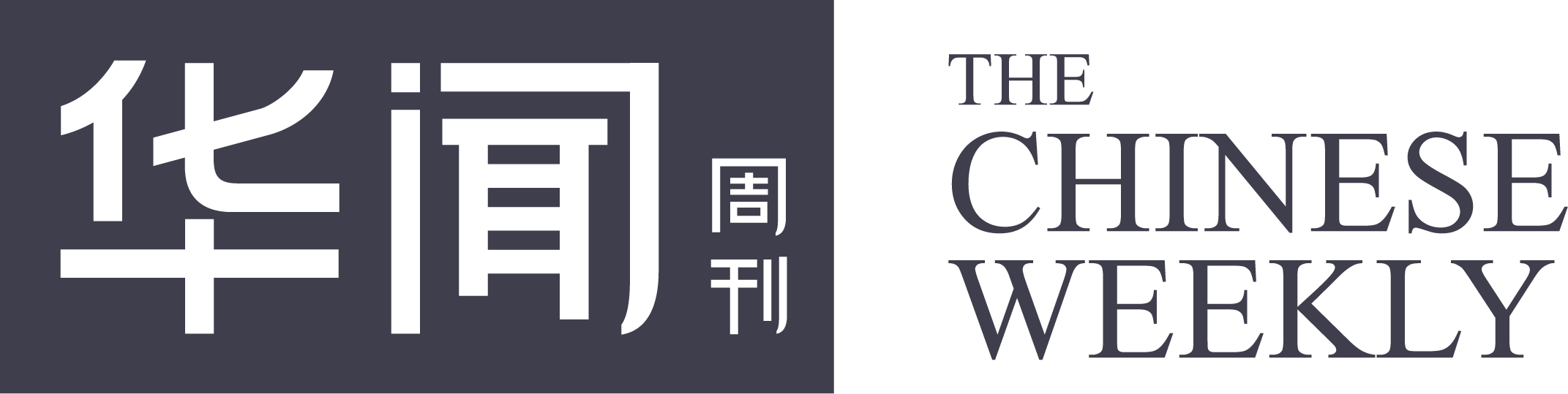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