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少年时代起,我受文学的影响就很深,尤爱描述探险与旅途的故事。从如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这样的经典名著到石田裕辅的《不去会死》骑行世界游记这类的流行文学,我都如噬书瘾君子般地啃读,这些精神食粮蓄养了我对未知远方的憧憬和好奇。终于在十七岁的某天,借由出国留学,我等来了远行的机会,可以亲身体会一下凯鲁亚克笔下的“可怕的大陆”。
我和一个父母朋友家的孩子,在长辈们的目送下,踏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西伯利亚火车。我们那次穿行欧亚大陆的旅行途经7个国家,穿越荒原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北上圣彼得堡,经由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欧的波兰和捷克,最后坐大巴前往伦敦,两个孩子跌跌撞撞有惊无险地平安走完全程,一路充满了第一次远行的兴奋与懵懂。如今距那次旅途已是四年,21岁的我在那之后再度两次在伦敦北京两点之间做过穿行欧亚的旅行,搭乘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大巴、火车,还有渡轮,每次的旅行路线不尽相同。在路上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交换彼此的故事,短暂小谈或相伴一段路后又各自航向不同地方。也有遇到过危险或者出乎意料的情形,好在最终都化险为夷,随着阅历的增长,惊慌失措的几率越来越小。旅途中有趣的片段串成一段段闪亮的故事在记忆之中发光,余味尚存。
西伯利亚铁路上的人
西伯利亚铁路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铁路,西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东至日本海海岸海参崴,横跨八个时区。铁路有两条国际支线,一条由莫斯科经由蒙古国乌兰巴托到达北京,一条经过满洲里到达北京。我经常选择的是途经满洲里的路线,因为可以跳过蒙古过境签。俄罗斯火车上的列车员有着俄国人特有的冷峻,与你对视时目若寒霜,你笑他不笑。一列车厢有两个列车员,昼夜轮换值班。他们不说英语,不说中文,我与他们交流只能依靠原始的手势猜谜,每一次交谈俨如一场手脚共舞。

在这条铁路上我遇到过患有恐飞症的法国作家,随身携带三万元现金的中国老人,携家带口一起漂泊的德国工程师,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做生意的中国商人,还有一次居然遇到了两个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外交官。法国作家和身“巨款”的老人是我在第一次的旅途中遇见的。因为火车在满洲里换轨需要六个小时,乘客都被迫到站台上自由活动,当时法国作家坐在站台露天的长凳上写东西。我之前在中国餐车(火车在中国境内为中国餐车,过了境换成俄国餐车)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他一边吃着糖醋里脊喝着啤酒一边在本子上做笔记。我走到长凳的另一头坐下,直觉告诉我他从事写作,于是我用英文问:“记者?作家?”“作家。”随后他在我的追问下告诉我他来自法国,靠写作为生,一路坐火车到北京,因为一直很好奇想看看中国是什么样子,在北京待了两周,现在又原路返回,之所以坐火车是因为有恐飞症。这位法国作家似乎有些腼腆,少言寡语,与他对话像挤牙膏,有点费劲。于是我还他清净,去满洲里候车厅旁的小餐厅和朋友吃午饭去了。

喝俄罗斯的经典菜式红菜汤时一个神情忐忑的老人过来搭话,在得知退休的他孤身一人要到俄罗斯和东欧旅行后,他递给我一个索尼卡片机,说“你看看这个怎么使?”我按了开机键相机没有反应,“没电啦。”我说。老人显出遗憾的样子:“那我不是白带了?”我问:“你没带充电器吗?”他语出惊人:“充电器?没有啊?”我们沉默了半晌,他又翻了翻贴身小包,递过来一个建行信用卡:“这个在俄国能用不?”没待我回答,他又拍了拍腰上挂着一个鼓囊囊的小包,说:“我就装了三万人民币,也不知道够不够?”朋友问:“你都装小包里?”答曰:“对啊。”我在心里真是为老人捏了把汗,一身现金走俄罗斯和东欧,真的可行吗?火车到达莫斯科后我再没遇见过那个老人,默默地祝福他一路风顺。
携家带口环游世界的德国人是我在上次旅途中遇到的,距今不过两个月。德国夫妇带着两岁的儿子尼古拉斯从北京坐火车到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一段时间。他们的儿子一头毛绒绒的蜷曲金发,欧洲小孩本身就长得极可爱,加上稚嫩的童音,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一路吸引了车上中国游客的注意力,单反镜头总是对准他。因为同在一个车厢,尼古拉斯总跑来我的包厢玩,爸爸或妈妈追出来,和我交谈片刻。六天相处下来,我得知他们从一年半前开始旅行,从德国飞到加拿大,租了辆车从加拿大开到美国,又沿着西海岸一路南下,结束了美国的驾车之旅后一家三口又飞到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他们买了辆二手车,深入澳洲内陆旅行了半年,最后来到中国北京,在北京短暂停留一个星期,坐西伯利亚火车到莫斯科,在朋友家住上一周,再回德国。他们启程时儿子才八个月,如今尼古拉斯已经两岁多了,可以称作是在路上长大的孩子,才两岁年纪走得路比许多成年人都多很多。尼古拉斯的爸爸在德国原本是工程师,工资很高,一年多前辞了工作卖了房子,带着存款和一家人上路,旅行已经成为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在我问到他们回到德国如何计划时,克里斯蒂娜说他们会先住到慕尼黑的妈妈家,等丈夫找到工作再搬出去。小尼古拉斯如今会流利地说德文和英文,英文都是在旅途中跟当地人学的。我想这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大概会让一些中国家庭大跌眼镜,原来孩子也不是非得在安定的环境中成长,只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就好。

有惊无险的两段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第一次远行的途中,因为年纪小经验不足,才出现了当时的情况。那是在圣彼得堡,我和朋友吃过午饭后往青旅走,在路过一个小喷水池时遇到一个发传单的人,硬往人手里塞。我们没理他,朋友在前我在后,大约走了七八米后路过一家店的橱窗,我无意间瞥了一眼橱窗,在玻璃反光中看到身后有一个人贴着我,手在我包里。我募地转身,眼前人手里正拿着我的护照,钱包掉在地上,可能是转身时从他手里扫到地上了。他见被发现了就用英文很快地解释说他见一个黑人抢了我的护照就追上他帮我要了回来,边说还边用手指着一条岔路示意方向,他说既然他帮我拿回了护照我需要给他四百卢布。那个发传单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也从他身后冒出来帮腔。朋友走了一段发现我掉队了就赶紧跑回来,因为朋友是男生,两个人便改口说一百卢布就够了。也是初生牛犊,有勇无谋的我趁他没注意一把夺过了护照,捡起钱包,拉着朋友快快地跑了,几十米外就是我们住的青旅。上气不接下气地检查了背包,所幸什么也没丢失。如果当时不是那个橱窗,可能真的就丢了护照困在圣彼得堡,一同丢失的还有护照里英国签证和欧盟申根,想想真是后怕。自那之后我在路上时都将挎肩小包背在身前,以防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人在旅途,即使经验丰富身经百战,人算不如天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下面的故事就是如此。欧洲之间的国际列车总是在深夜抵达。巴黎到莫斯科的高速列车在八点二十八启程,两天后在夜里十二点半到达莫斯科,我在中间站柏林上车,一天一夜后到达莫斯科晚点了两小时,到达Belorusskaja火车站时已是凌晨两点半。由于我独自旅行,考虑到半夜抵达,启程前我在booking.com上订了位于火车站二楼的一家青旅,本以为这下万无一失连车站都不必出,谁料两点半候车楼已经锁门了,根本进不去。不知所措的我背着四十升的行囊冒雨绕着车站走了两圈都找不到其他的入口,终于找到一个小通道后就怀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走了进去。通道走着走着逐渐向下,光线愈走愈暗,后又遇到一段旋转楼梯,石阶上有积水,上到一楼遇到一个堵死的通道门,门前设了生锈的铁栅栏,一盏照明灯忽闪着发出电流的嗡嗡声,整体气氛堪比库布里克的电影《闪灵》,就差没遇到一对复活的双胞胎姐妹。我硬着头皮又上了层楼,这次楼梯在中间就被堵住了,幡然醒悟的我终于意识到不对,掉头就跑,一路跑下楼梯穿过通道,回到下雨的空旷的街上。最后绝望的我转回火车站的站台上,找到了个穿着类似保安的人与他交谈,我把预订青旅的订单拿给他看,因为他不会说英文就又带我见了办公室里值夜班的另一个人,磕磕绊绊地沟通后他们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打开了候车楼的门。一番折腾待我进入房间已是四点多,这时我才把一直攥在手里的报警器和喷雾器松开。

青年旅社的一次奇遇
此事发生在布拉克一家受欢迎度排名前三的青旅内。我和朋友住在男女混住的八人房内,与我们同屋的有两个伦敦的姑娘。我们晚饭后回到青旅,碰到两个姑娘正要出门,招呼说要去酒吧一起去不,因为白天把精力都消耗殆尽,我和朋友婉拒了他们,稍作整理休息了。大约三个小时后,我被走廊的嘈杂声吵醒,仿佛有人在吵架,其中有一个女孩的声音,似哭非哭,似笑非笑,还有两个男人的声音在争论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原来伦敦的一个姑娘不知被灌了什么药,神智已经不清醒了,另一个姑娘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其中一个男声来自把姑娘从酒吧送回来的人,另一个男声是青旅的前台。前台不让陌生的男人进到青旅,男人在解释酒吧里的事。最后前台搞清楚前因后果,把神智糊涂的姑娘安顿到床上。姑娘一直在呻吟着哭,一屋子的人都醒了,默默听着。大约半个小时后,另一个姑娘也被同一个男人送回来了。这次前台因为有先前的事就让男人进来了。后面的姑娘大概只是有点醉,还算清醒,她和送她回来的男人进屋后就滚到床上了,屋里除了我和朋友还有另外四个人,震惊又尴尬地一言不发地听着。事情的尾声是神智迷糊的姑娘找不到洗手间,在屋里小便失禁了,同屋的一个法国男人终于忍无可忍把她轰了出去。如此一夜,屋里其他六个人自然谁都没怎么睡。之后我在网上读到过顾客投诉,那家青旅的受欢迎度想必多少受到了些影响,或者也有抱着猎奇心态慕名前往的人也说不好。

旅途中形形色色的人与事足以写成本书来。每场旅程中都有无数小的散场与相遇,时常旅行的人对人与人的散场大约都已习以为常,而小尼古拉斯在每一次与人分别时都嚎啕大哭,抵达莫斯科那天下午他哭了一路。西伯利亚的荒凉广漠,欧洲城市沉厚的文化,自然与人类文明的结合贯穿一路,作为摄影系的我一次次地感受到某种召唤而上路,随身带着相机与笔记,结合图像与文字点滴记录。在路上的我们都是小人物,怀揣着各自的梦想与渴望启程,恰如少年歌德写的那句话:向天上他向往最美的星辰,向地上他向往所有的欲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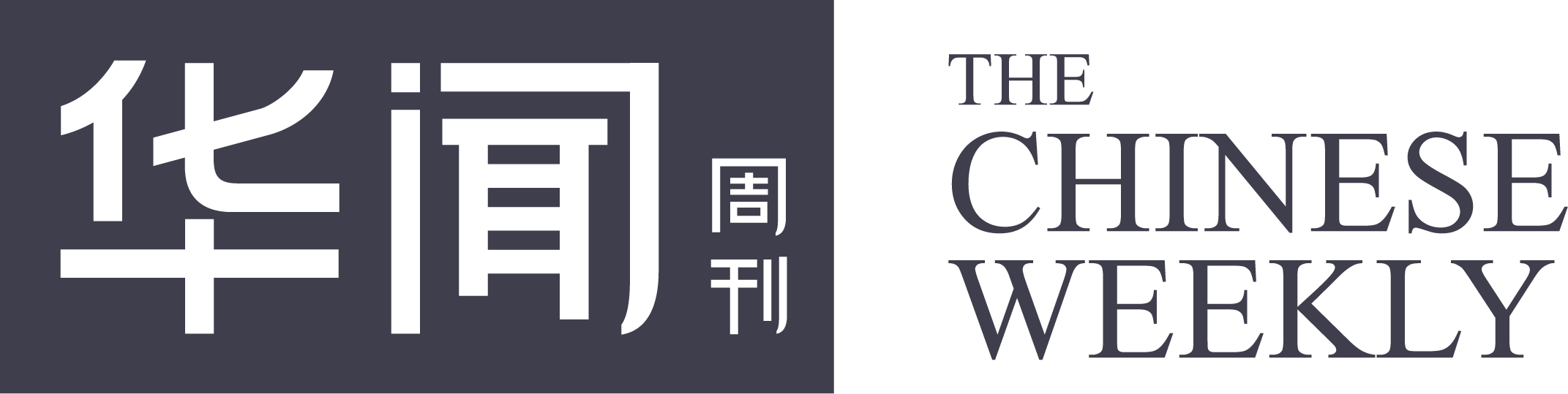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