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卷语:庙堂和江湖之间
上周的日子过得实在闹心。
伦敦地铁工人闹罢工,英格兰西南部闹洪水,苏格兰继续闹独立。除了洪水是中国人常见的,另两个似乎都是“有英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后期阶段”之特有事情。听这些事儿的名头,我等天朝英漂深深地为卡梅伦同学头大,但英国人却完全是一副习以为常的态度,马照跑,舞照跳,球照踢,酒照喝,唉,真是蛮夷不知亡国近,隔洋尤唱Mind the Gap。
在英国,罢工是生活,更是奇特的政治博弈。以2月4日至6日的伦敦地铁大罢工为例,一方是伦敦铁路、海运及运输工会(RMT)和领薪运输员工工会(TSSA),另一方是伦敦地铁公司(London Underground),这是形式上博弈的双方,但事实上牵扯进这件事儿的利益方可并不止这两家,比如需要天天坐地铁通勤的普通民众,他们是意见和选票的末端,每个人都可能是一根压下天平的稻草。
这次罢工的原委是这样的:伦敦地铁公司打算推行地铁“现代化”的项目,以便能够省下大量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将设立更多的自动售票机,以取代部分人工的售票亭,并进而大规模削减工作岗位,这自然引起了利益受到损害的地铁工人的不满。RMT和TSSA两大工会由此提出反对,并发动了48小时伦敦地铁大罢工;2月11日,由于双方的谈判取得进展,并暂时达成和解,RMT和TSSA终于宣布取消了拟定于2月11日至12日进行的第二次罢工。
切不可高兴得过早,另一条新闻来了:英国全国教师工会(NUT)宣布,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中小学教师将在3月26日举行全国大罢工。
在英国,工会组织的“罢工”实在是家常便饭,从筹备到实施,罢工大都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人们很难从法律层面对其进行指摘。那可真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典范。而它能否被取消,全看各利益方如何博弈,可以吵得脸红脖子粗,但最后必须握手达成一致,不能掀桌子抡菜刀。我们的一位专栏作家打了个比喻:“英国的工会与资本家的关系如何?他们犹如迪斯尼卡通片里的猫和老鼠,既是死对头,又是一对儿欢喜冤家。”这是光明的游戏,也是智慧的较量。参与的各方斗智斗勇,比的是谁更沉得住气,谁更输得起,谁更经得起折腾。在一个依法折腾绝不会被抓捕或劳教的国家,折腾成了文明的一部分。
本期专题对此做了详尽的采访和调查。我们采访了工会人士、学者,也采访了普通的民众。作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对于工会的地位和罢工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讽刺这次罢工是“以影响大多数人利益为代价的小长假。”也有人说:“罢工是不负责任的,解决问题和争议不应该只有罢工一种方式。”但也有人认为罢工是“可以理解的”和“正义的”。
当工会组织的罢工发生时,作为一个深受影响的普通人,我为它给我的生活带来的种种不便而忧心,便有一声喟叹:“工会司机,宁有种乎?”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主张消除工会这样的独立的利益团体,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权力制衡的体系中,正是由于有着多元的利益各方的存在,才使得整个体系保持了健康和平稳的发展。任何一方的突然消失或缺席,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整个体系的失衡,甚至崩塌。
在2月8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行的“中国发展论坛”上,我听到了一个绝妙的言说,和我们这期的专题想要探讨的问题也有着潜在的关联。这个论坛的主题叫做“寻找新的平衡”,演讲的嘉宾们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出发,谈了各自的看法。
“明日中国”基金会的廖立远在演讲时,提到了中国古代的一个名人——范仲淹。老范的那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实在是脍炙人口。但人们很少来思考,老范为啥总是忧心忡忡,幸福指数怎么就这么低呢?为什么他居庙堂之高的时候也忧,处江湖之远的时候也忧呢?
在廖立远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在庙堂之高(体制内)的时候,他必须按照庙堂的规则来办事,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可能以一种独立的姿态来发声;而当他不在庙堂之中,而处江湖之远(体制外)的时候,他又没有这个能力和权力来做事儿了,因为在中国,权力和资源大多集中在体制内的少部分人手中。所以老范之所以忧心,实在是因为在中国从古至今的传统之中,除了庙堂就是江湖,两者之间没有其他力量存在的空间。而如果老范在英国,他还可以在庙堂和江湖之间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角色,比如给政府做做咨询,也可以担任游说者(Lobbist),甚至也可以参加类似工会这样的压力团体。
在随后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的交谈中,我听到了另一个有趣且异曲同工的说法。贺卫方说,真正的和谐应该是一种差异得以呈现后的和谐,“什么时候在我们的决策出台之后,能够把反对的声音也呈现出来,能够把领导层、立法机关以及不同权力之间的冲突都展现出来,我们的政治文化才可以说是发生了变化。而只有政治文化发生了变化,才会对体制产生影响。”他认为,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需要的是一个利益更加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有更多独立的、多元化的组织来制衡权力。
这是来自中国的学者以及专业人士正在思考的“寻找新的平衡”的方法。
当然,这种方法在英国早已用了很多年。但这种处于庙堂和江湖之间的第三种独立的力量,其实也有着好与坏的两面。当它过于强大的时候,往往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上世纪70年代,英国工会势力处于顶峰时期之时,三天两头罢工,日子没法儿过了,谁也受不了。到了撒切尔夫人上台后的80年代,对工会采取强硬的压制政策,后来布莱尔时期的新工党也有意识地拉开与工会的距离。但却正是在这种政府、政党、民众与独立的压力团体的权力博弈中,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得以达成。
如果把这些压力团体的各种行动对我们构成的冲击看成是一种“生活之重”,那么它的消失所带来的权力失衡,则可能会成为一种深不见底的“不能承受之轻”。而后者似乎比前者更为危险。
想到这个层面,我们便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有效地把这种“重”限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是靠体制,还是靠文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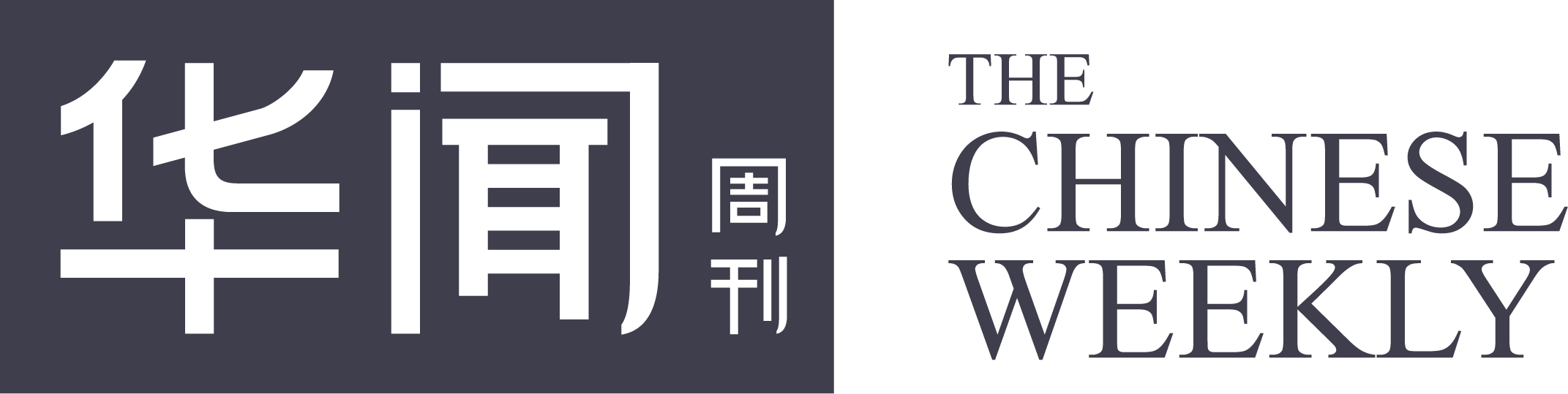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